另类空间,另类策略
| 2011年01月31日

中国艺术界一个被人议论最多的特点就是其高度商业化的画廊体系。基本属于西方舶来品的画廊体系在过去十年迅速发展成熟,并成为中国艺术家和国际艺术界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不管怎样,画廊及其代表的商业体系主宰着中国艺术界,伴随它们成长的还有不同艺术区(包括北京的798和草场地,或者上海的M50),后者是国家认可并支持当代艺术经济文化实力的明确表现。
然而,这一发展似乎是以牺牲批判性参与和更大社会意义为代价的。如此庞大的产业化系统很有可能导致当代艺术整体停滞不前。当然,这种状况似乎是由于中国加入国际艺术界的时间尚短,虽然活跃,但仍比较稚嫩,即中国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一套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成熟的艺术体系。

但已有一批艺术家和机构在积极寻找出路。他们有意识地跨越艺术机构、作品和社会之间的界线,关注问题的同时把意义和边界拓展到新方向。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相对独立灵活,因此可以较为公正地对体制提出批判,而不至于招来任何致命的后果。某种层面上,他们的资本在于智力和社会含义,而不在财力,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可以坚持自身立场,对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或社会进行批评。
这些“空间” 尽管只有一部分是永久性的实体空间正在为现有体系增添对比区别和批评的方法论元素。这些个体或组织深知自己的活动与中国艺术界批判性较弱的部分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针对目前艺术界及其所在社会的各种问题和争议,他们总是积极推进那些足以产生突破性进展的作品和行动。
虽然“另类”作为一个讨论出发点并无不当之处,但对于这些空间来说,称其为“另类”可能有失公允。“另类”常常让人想到“对抗”,但这些艺术家或策展人更多是从“补充”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他们并不是单纯为了与众不同而选择“另类”,而是希望能以此超越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也许“另类”概念本身就处在批判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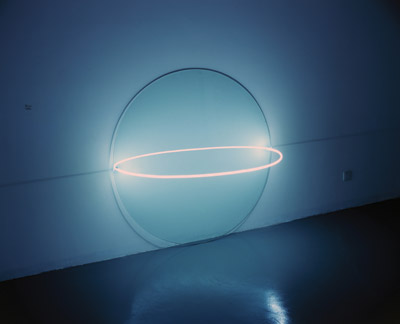
比如,“另类”反对的并不一定是商业化本身,而是那些目前中国艺术界中比比皆是的毫无批判性的商业化模式。这些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看似已经非常僵化的画廊形式:无法呈现某些类型的作品,只允许特定渠道或形式的活动进入空间。“另类空间”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是:表面上独立于画廊系统之外,但为了自身目的又与之保持某种联系;必要时自由出入于不同的艺术结构。很多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画廊、正式展览或传统艺术结构。他们不想积极地去“反对”谁,而是在介入和脱离之间按照自身信念开心地做着选择。针对令人窒息的系统和结构,他们的回应行动常常是微妙而隐蔽的。
举几个例子:家作坊通过小小的店面将艺术实践引入胡同语境,在社区里推动在本地的社会活动,从而将事件从日常活动中“提炼”出来。驴子当代艺术协会把艺术直接带到流动的公共空间,用移动模式对其进行重新定义。陈昕鹏去年以帐篷为载体的流动展览“凑和”(红盒子工作室策划)同样将艺术家的活动带到非艺术领域,旨在激发自主式展览和令人兴奋的创作实践。马永峰和他的forget a r t小组重访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以玩笑的手段挑战中国机构化的艺术模式,他们最近还在一个洗浴中心策划了一场展览。植村绘美在中国食品和农业现实的背景下展开讨论,从自身具体处境出发直面社会问题。
和这些艺术家、策展人谈话的过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们如何通过艺术创作过程起到助推器和平台的作用他们的答案也暗示在现有机构和运作方法中,这一功能是很难或不可能找到的。而上述活动背后似乎潜藏着一种感觉:经过重新组织和自然化,如今的艺术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生产体系,和其他任何生产体系毫无二致,不具备丝毫特权。所以他们对商品化和商业化的系统力量保持警惕,对艺术不像前人那样满怀敬意,而只是将其作为选择性使用的领域之一。

这些方法和实践在国际艺术史语境下并不少见,其实等于梳理了西方艺术史各流派中有关艺术特权地位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这些艺术家超越传统之处就在于他们与中国具体环境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富有原创性。在中国,上述实践算是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此背景下,也就有可能为将来的艺术活动带来新的可能性,而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同辈们也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回应。这些可能性不仅针对现有系统,更以其非物质或非永久的行动在不“生产”的情况下赢得了空间。这些作品看上去是疏离的,所维系的
关系并不能完全归于某个特定目的。这种没有既定目标或预期结论的半成形行动通过避开一般政治活动(效果可疑)的常见形式带来了某种政治结果,在这样一个外表决定一切的环境下似乎尤其合适。而且,正如在其他地方的同类实践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此类行动要在通向生产的道路上被无限搁置其无效性永远处于一种引而待发的状态,但这种“搁置”和“无效性”又是保证行动可能性的关键所在。

上文列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从本土化生产开始,这对于建立意义容量更大的艺术体系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另类”空间的创作活动将目光对准系统内部可见的问题和缺陷,它们的存在对批判艺术观念及其传播方式不可或缺。实验和展示的新形式能够为艺术界带来更大的深度和更丰富的见解,除此以外,当我们遇到有关艺术及艺术体验场所等问题时,这些实验和新形式也能防止我们过度依赖极具局限性的少数视角。所谓“健康的艺术生态”必然支持这些多样化体验场所的成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足够的制衡机制,避免系统的某
一个部门以偏概全,进而扭曲了艺术的视野和价值,而这 一点在我看来也是目前中国艺术圈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