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若汐(Solveig Suess)和艾莎·巴兹列娃(Asia Bazdyrieva)二人组成的艺术小组Geocinema(地理电影)探索电影与星球之间的关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用户及设备所捕捉的图像不断增加,地球表面的记录愈加详细。地理电影小组对地球的数字化网络背后的基础设施进行深入研究,将其想象为一台庞大的运动图像(moving image)设备。各种技术都以不同的规模为地球的数据收集工程助力,其中涉及企业与政府的协作,二者都从这个分布广泛的素材网络中提取信息。越来越多的视觉、听觉和地理数据被应用于从个人到全球再到天文级别的监视,同时也被用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地理电影的工作凸显了政策与实践、整体与局部、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张力。
曲若汐是一名纪录电影制片人和研究者,具有视觉传达和建筑学的学科背景。艾莎·巴兹列娃是一名艺评人,曾在哲学、化学、艺术史和建筑领域受到训练。她们就地理电影小组的研究视野和工作方法与作者和策展人曾明俊(Billy Tang)进行了对话。Billy Tang(以下简称BT):你们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以双人合作的形式工作,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Solveig Suess (SS):2018年我们都在斯特列尔卡(Strelka)媒体建筑设计学院的“新常态”(New Normal)智库担任研究员,合作就从那时开始。尽管那时是在机构的框架里,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兴趣,且一起工作时能够相互启发,这个项目里大多数的实验都还在继续。
BT:所以“地理电影”是小组的名字,还是特指从你们的合作中生发出来的作品?
SS:我觉得我们已经逐渐把这两者混为一体了。它既是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合作的化名。陆地卫星镜头,NASA公开档案,电影《制造地球》静帧,2020年
BT: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说都很重要的社会其他领域的交叉点, 以及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否和电影的历史发展有联系?Asia Bazdyrieva(AB):“地理电影”最初的概念是把星球尺度的传感网络视为一种分布广泛的电影设备,一台摄像机。在这里,图像和记录仪器的概念已经被扩大,并被嵌入到地理构造甚至社会政治的结构中。当我们说地球的表征从不完整时,我们直接借用了蒙太奇的概念。我们对电影的兴趣和联系是指这种把时空媒介化的技术,这种技术创建了有效的反馈系统,并通过运动图像在我们的视觉神经和感官经验之间的循环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代理形式。从20世纪在光学仪器上巨大的进步中可知,运动图像既可以作为一种客观化工具,又可以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实践而使用。正是由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热衷于将运动图像的思想从它的物质层面扩展到其所能实现的关系上——既解决现有光学系统的偏差,又考虑其替代者。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系列的方式来组织工作的,每一个都探讨了图像和电影感知的各个方面。SS: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将最近的案例研究和更长久的摄影及图像文化联系起来。例如,只能被自动驾驶汽车之类的机器所读取的图像,或仅供工作人员阅读以检查生产线上产品质量或在过安检时记录的图像。从科学与测量到资本和劳工的控制,这些图像被使用在各种操作上。它们过于丰富的记录、存档和分发,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压倒性的……当然了,电影和制片的发展一向是和新的光学与记录方法缠绕在一起的,这些方法不仅出于电影业、还出于科学与军事的目的得以开发。所以对我们来说,“地理电影”项目作为一种方法,既能帮助理解这些图像如何在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理解环境自身如何结构和形成这些图像和它们的循环。图像实践者和理论家如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崔佛·帕格伦(Trevor Paglen),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和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率先开展了广泛而重要的工作,通过“操作图像”或“后勤图像”这两个术语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国,乌克兰还是其他国家,我们都希望处理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或政治利益更接近的地方。借用一下媒介理论家尤特·霍尔(Ute Holl),她谈过电影界如何退回到思想、设备、工业和景观的子例程中。在这个更宽泛的概念下,这就是当我们用“电影”(cinema)这个词时想要坚持的东西。因为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老派的单词,但当我们把“电影”理解为进入共享空间的集体经验时,它作为思考的棱镜就变得富有成效,尤其是当它跨尺度移动时。BT:在你们的实践中,有什么常倚赖的方法或工具吗?比如你们进行的田野工作,或者广义上的跨不同领域工作的策略,以及你们提到的地理位置?SS:“地理电影”也是一种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想直接与这些系统内的表征作斗争的,于是电影制作既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模式。AB:这种表征的挑战是我们对研究和拍摄电影进行非常清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今天的大多数成像技术都无法以被人类立即看见或察觉的方式进行操作——它们太复杂,太分散,太快。同时我们也被移动和组织它们的图像和算法支配;我们的感知在许多层面上都是预先编程的。如何去表征这些自身无法感知的复杂系统及其机制呢?我们的方法是采用支持传感和成像技术的基础设施,并进入构成星球级电影过程架构的各种空间。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定义了我们的田野工作方法——我们从物理上跟随图像的形成——而主题本身使我们可以从各种研究领域中借鉴,例如批判理论,女权主义认识论,激进地理学和媒介理论。SS:我们欣赏纪录电影的一点是,它关注过程。当我们在田野工作中开始去理解这些大规模的记录系统是怎么发生时,当我们真的使用一台摄像机去记录我们的遭遇和对话时,在我们与其他人在声音、运动图像和文本上合作的整个过程里,我们回转去思考这些围绕现代性、电影、美学和认识论的宏大问题。所以我们经历了重新聆听、重新观看、剪辑和讨论的过程,处理这些场景、建筑、对话,以及与其编辑形式和经历的动作直接相关的情感。我们经常从女性主义政治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时空的影像及声音材料剪辑与拼接,无论内容多么宏大或普通——在我们的情况下通常为后者。北京古观象台,电影《制造地球》静帧,2020年
BT:能否介绍一下你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新项目的大致概念?
AB:“架构区域”(Framing Territories)是“地理电影”系列中的一个。它探索了地球图像和地形之间的关系。我们感兴趣的是,用于观察地球的光学系统如何融入开发攫取活动,并最终进入到如全球变暖之类的庞大之物(hyperobjects)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称之为“数字一带一路”(Digital Belt and Road,后简称DBAR)的项目,是一带一路的数字副本。这个项目由中国政府发起,但也是杂糅且国际化的。DBAR项目致力于设计一个国际平台,能集合地球观察数据,以规避全球变暖相关的风险。所以这实际上是获取更多地球的数据以对它进行更多的榨取和开发,同时还能意识到其中涉及的潜在风险,可以抢先做出决定进行应对。这是一种奇怪的局面:为避免全球变暖而制造出来的东西,首先就引起了全球变暖。保护地球的观念如何与开发地球的观念同时出现,我们对此非常着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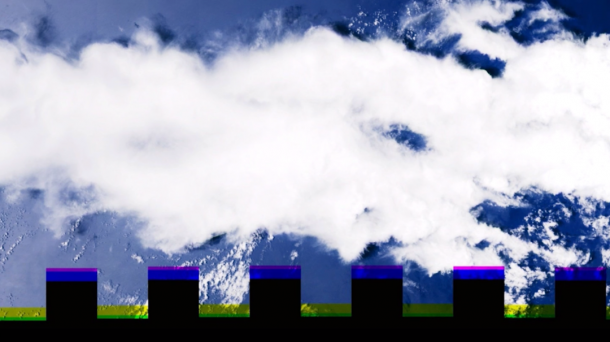






泰国是拉差县GISTDA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电影《制造地球》静帧,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