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的罅隙间生长:从女性主义出发的青年从业者手记
| 2023年07月25日
从新冠爆发前夕至今,中国正经历一个从隐到显的“脱钩”时代——起初的“例外状态”转为常态,常态则转为“非必要”。冰冻三尺,确有三年之寒。无需赘述漫长的新冠流行和防疫对各行各业的冲击,在2022年的凛冬来临之际,作为一名青年艺术从业者,我试图从自己的观察出发,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回溯三年中的一些碎片感受。尽管这些体会是如此主观而可能充满纰谬,但却忍不住提笔记录,或许因为我一直坚信主观感受自有其价值,艺术就是最好的明证。
2019年8月,我加入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担任策展人,9月启程前往巴黎出差开启新展筹备工作。本以为与国际艺术家的线下交流是寻常之事,没想到,2020年初这一切骤然改变,绝大部分的沟通被迫转移到赛博空间。我和同事们一起从零开始,探索在无法见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100%远程协作”策展和布展。三年间,我个人深度参与的各类展览项目就有近十个,覆盖了UCCA位于北京、上海、秦皇岛的三处空间。其中无一例外,都需要大量的线上沟通。
时至今日,这一危机模式仍在不断延续,看不到终点。在政治性抑郁的晦暗中,我想继续保持警觉与愤怒,也想记录下这段歧路上发现的光亮,它们虽微弱,却在罅隙间闪烁。这些微弱的光亮远不足以慰藉寒夜的行者。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期待着冬去春来的一天快些到来。但如果可以从雪被下的寂暗中识别幼苗,保护和照顾好它们,雪融之际,我们当创造一个更蓬勃的春天。
I: 智识开源与数字化身
前疫病时代,线下会议和讲座受时空与经费所限,参与者寥寥而多为“精英”。虽然当时也已经支持音视频转播,但线下形式还是绝对的正统与主流。“大流行”开始后,人们不得不选择远程办公,也加速了各类会议、讲座“上线”、“直播”、“开源”的进程,逐渐织就了与肉身困境大相径庭、无远弗届的数字智识网络——即便没有发生实际位移,人们也可以通过线上会议和讲座开展工作、参与讨论、获取知识,甚至可以同时身处多个虚拟会场。
在美术馆工作场景中:与国际艺术家、机构同行、策展人、研究者的高频线上会议和讲座逐渐成为常态。虽然这样的形式也引来了诸多批评:消耗大量时间、注意力碎片化、缺乏情感共鸣和具体的连结,但不可否认,参与“门槛”的降低实际惠及了较年轻的从业者们(也包括我自己)——以往这些需要差旅的会议壁垒森严,而现在,轻点一串链接就可以参与“居庙堂之高”的内部会议。线下转线上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在场的机会,即便只是聆听,这样的机会也是宝贵的。
另外,赛博空间的交流无形中消弭了参与者在体型、形象、声音等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导向了一种去中心的“均质化”。终端界面提供给用户尺寸统一的显示框,相近的声音输出,有限的社交手段(如抽烟、喝酒、饭局)及个人信息披露。在国内行业场景中,被这种“均质化”赋权的人群,多为现实交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必然是女性,却不难想见女性居多。在线下,女性暴露于更全方位、高强度的凝视中,而对她外貌、着装、肢体语言的关注往往会稀释其职业属性。“数字化身”为女性以“去性别化”的姿态登场提供了机会。而我深感在当下身处的职业语境中,这确有助于将注意力转移至女性的职业素养,为她们提供更公平的舞台——即便这一公平达成的方式是让个体隐蔽、而非显露。
我深知对“去性别化”的赞许其实饱含着“厌女症”的倾向,但就像上野千鹤子所说,“女性主义者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1]希望终有一天,无需借助数字滤镜,女性能摆脱所谓“女性气质”的困扰,以参差百态坦然地在职场呈现自我。

II:“代理人”与“大师课”
尽管中国艺术行业中的女性从业者绝不占少数,女性主义也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已经挣脱了由男性设定的行业规则:大部分女性从业者徘徊在行政与助理属性更强的岗位上,能接触策划、经营、管理等核心职能的仍是少数。
在新冠大流行前全球艺术交流如火如荼的时期,邀请海外艺术家、策展人、技术团队前来中国访问及布展是行业惯例。中方美术馆员工(大部分是女性)的职责集中在组织交流、协调配合上。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两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当代艺术系统,“边做边学”是一种常态。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女性同行,她们蛰伏蓄力已久,但一直缺乏自信和机会。当然,我也在反思这种“乐于处于幕后”的状态是否本身就来源于女性长期受到的性别规训——“女性习惯于谦逊,万一她们越过了这一既定的性别准则,就可能受到惩罚”。[2]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的新冠大流行与延续至今的旅行限制,这种状态可能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2020年,随着情势的变化,国际艺术家与合作者面对鞭长莫及的中国项目,亟需寻找本地“代理人”,不折不扣地实现既定目标。好的“代理人”必须足够了解艺术家的思想与创作,甚或将自己转化为一种艺术家的“分身”,在面对层出不穷的困难时做出及时而明智的判断与应对。机会与挑战于是同时降临到年轻的从业者身上,她(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从“助理者”成为“代理人”,在拥有了决定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
回顾过去三年主责的几个大型展览项目[3],我深刻意识到,疫情所造成的“断裂”在戏剧性地加大工作难度的同时,也创造了出人意表的机遇。许多艺术家可谓倾囊相授、巨细靡遗:从创作理念到作品结构,从材质到代码——犹如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师课”。当一切最终凝结为心有灵犀的默契时,“代理人机制”或许意外成为了年轻从业者从青涩走向成熟,由幕后行至台前的加速器。
当然,我必须再次重申防疫对整体环境的打击,也无意在任何层面美化现状,但这些充满矛盾的真实观察确实是我撰写此文的最大动因。希望“代理人”们经历的这场突如其来的考验能在后疫情时代给予他们更多自信去迎接新的挑战——或许是成为自己的代理。

III:身边的西西弗
此时此刻,人们无法预知明天能否正常踏出家门。在笼罩着不确定性迷雾的时代,直面层出不穷的“不可抗力”、应对“没有结果的付出与无缘无故的丧失”成了沉重又普世的课题。艺术行业中,延期、调整、重头再来成为常态,所有人都切身感受着西西弗之苦。但对众多女性而言,这种苦楚或许并不是全新的经验——想想那些由她们主要承担的,周而复始的家务与照护工作吧——不成正比的付出与收获之于女性并不陌生。从月经周期到孕育生产,女性与“不可控的身体”长期共存,生活往往“被打断,然后重头开始”。
女性被这样的生命经验磨练出的韧性与耐性、敏锐的洞察、沟通与共情在这场危机里编织出一张抵御破碎的网。她们不惮于将热情与劳动投注于可能无所回报之事,在转瞬即逝的空隙间不骄不躁地垒砌砖石。过去三年的工作中,我一次次被同行们百转千回的努力而震动,并坚信她们正在“给虚无涂上色彩”。[4]2022年春天筹备托马斯·迪曼德于上海UCCA Edge的展览期间,我与女性占多数的团队一起经历了两个月的严峻封控。在漫长的等待与煎熬中,大家奋力维系着联结:四月,我们关心彼此的食物短缺,尽己所能互相照拂;五月,还见不到面,就一起线上看电影,在孤独与愤懑中交流取暖。为了让远在柏林的艺术家理解上海的事态,我们每周制作“疫情发展及防疫措施报告”发给德方的艺术家工作室,唤起不在场的伙伴的共情。到了六月,团队在依然极不稳定的状态中紧急重启工作,应对意想不到的各类困难——工人们经常因为随机被封无法按照布展计划施工,需要随时随地调整安排。七月,展览终于开幕了,三月就已经在展厅铺设完毕的粉色樱花墙纸在等待了整整四个月后终于与观众打了照面,冥冥中像是我们对这个“失去的春天”最好的纪念。
我的团队中既有女性也有男性,但我想表达的是,社会偏见往往认为女性占多数的团队会形成“雌竞”[5],而我们分明已经书写了一个新的脚本去呈现女性群体的故事。我真切地受惠于女性同盟的友爱与互助,是她们用智慧和情感在孤绝间架起了充满韧劲的桥梁。而且,这并不妨碍她们同时拥有勇气、决断力和行动力,所有这些品质不该只属于特定的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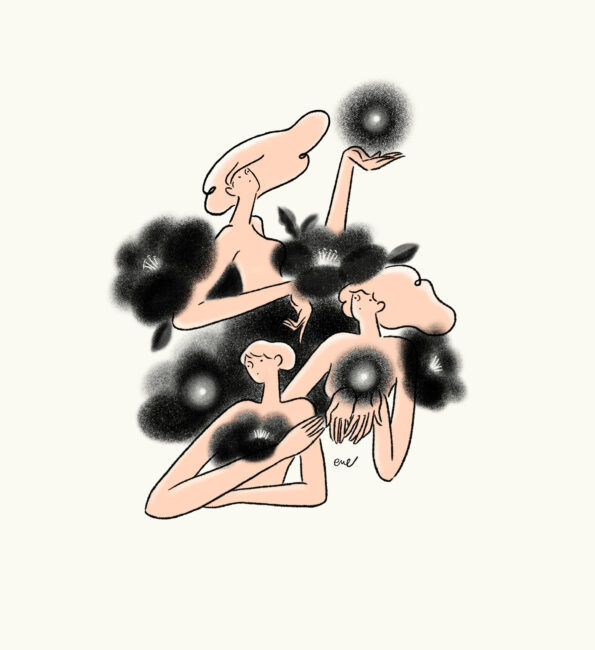
尾声:自灯明
短暂又漫长的三年改变了几乎所有事。这篇写在11月末的手记所记录的微弱光亮在肆虐的风暴前可能不值一提,但却是我真诚的感受。
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提及“自灯明”一词,意为“在黑暗中行走时,依靠微弱的亮光照亮自己的脚下”,而为点亮黑暗而燃烧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6]这也让我想起这些年被反复援引的鲁迅先生“萤火”与“炬火”之说。如今,等待“炬火”已三年,仍是万马齐喑,或许本就没有什么“炬火”存在,暗夜里,只有点点萤火之光才是希望所在,照亮自己脚下,也照亮了同行之人。
如此足以,是以为记。
[1]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233页。
[2]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110页。
[3] 具体的项目包括涉及近30位国际艺术家,70件作品的“非物质 / 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UCCA 北京,2020);与匹兹堡安迪·沃霍尔美术馆合作,呈现近400件原作的安迪·沃霍尔回顾展(UCCA Edge,2021);德国艺术家托马斯·迪曼德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托马斯·迪曼德:历史的结舌”(UCCA Edge,2022)
[4] 加缪:《西西弗神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
[5] “雌竞”:女性们站在父权视角凝视其他女性,并因此对其他女性产生敌意、进行批判。
[6] 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227页。
秋韵是独立策展人,曾担任 UCCA 龙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部副总监及策展人,龙美术馆、乔空间策展人,并深度参与了 UCCA Edge、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筹建工作。
她擅于策划和管理大型国际艺术展览项目,长期关注年轻艺术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的发展,致力于构建更可持续的当代艺术生态。
插画:尹小为E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