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如果话语不合身
| 2023年07月14日
我
2021年的十月不像今年这样燥热,隔离近半,从半开的窗户探身出去能嗅到桂花香气。这阵香气绵延了将近一个月。站在上海街头时,甜腻随风窜入鼻腔,令人浑身一颤,为身在湿润温暖的中国南方雀跃。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发展出了“风土学”,颇为本质主义地说,人们被气候、地形、水文孕育,也投身和显现于自然,在其中观察自身和整体意义的“人”。中国人的性格,被他划作季风与沙漠的叠加——他在昭和二年(1927年)的上海目睹了北伐战争里的中国人。那时候的老百姓即便共产党人的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没有政府指望,也“悠然不迫”地照常度日[1]。当时或许和现在一样:要站在街头,才会意识到在微博上蔓延的地狱新闻和政治性抑郁之外,还有一片风土。桂花盛开,卖玉兰花手串的阿嬷提篮兜卖。在许许多多的门口,我和保安心照不宣地摆摆手机,不改颜色。

“年轻的机构”论坛现场,明当代美术馆,上海,2021年10月10日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出隔离的第二天,我和伙伴跑去明当代美术馆听论坛,论坛主题是“年轻的’机构‘”。国内的朋友说,你刚回来,这是个了解国内生态近况的好机会。穿过投影仪、显示器和帘幕的阵法,猫身坐进美术馆楼梯改成的观众席,两旁墙壁上滚动着标语突然抢入视野,每个字都在暗光中闪烁不停:
……尽管你看不见,但我们依然紧紧相连。欢迎进入流动相依、关怀社会的替代时空,尽管你看不见,但我们依然紧紧相连。欢迎进入流动相依、关怀社会的替代时空,尽管你看不见……
眩晕。字条喋喋不休,乌托邦气氛漫溢。口号跳过了“我”,从“你”跳到了“我们”。这场活动的组织方“雷电所”是家科技艺术策划和艺术家孵化平台,由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雷电所是明当代当时展览的组织者,也是这场论坛的召集人。我好奇在今天大陆艺术和商业跨界的语境里,实践者为何仍然执着用“机构”或者“新型机构”这样的词汇[2]。《辞海》说机构“泛指机关、团体或其他工作单位”,但“艺术机构”里的“机构”常常对应的是英文里的institute,这个词在韦伯斯特辞典被解释为“具有特定目标、常和某个事业(cause)或研究领域相关的组织”[3]。“Cause”作“事业与目标”之意时隐含着强烈的价值认同。如此一来,“艺术机构”,除去受到纳税人的税金资助要有公益性质之外,隐含的意思便是去问艺术的方式及其目标,与众人的生活有何关联。
2019年的冬天,在798的东八时区,时任长征计划(Long March Project)总监的梁中蓝(Theresa Liang)反问我,“我们总在讨论长征计划是不是一个机构,可是在大陆,你觉得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机构?”在2010年代的语境里,长征计划因为与长征空间画廊共享资源而需要为自己的非营利性辩护、争取被识别为“机构”,一种为了公益而非私利的形态。再往前倒十多年,长征空间的前身两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却能堂而皇之地展露自身的复杂。2005年,长征的英文网站上如此描述,“与其说长征是间画廊,不如说它是一个中心、基地和工作站,期待连接艺术世界与中国社会、中国与世界。”[4]卢杰当时用“黑白红”描述中国的艺术生态和长征的位置———“一个地下独立的,我把它叫做黑道;国际机构和老外是白道;另外还有一个红道,就是美术馆和美术学院。无论是哪个结构,彼此暖昧,彼此混合,彼此依赖。[…] 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都在工作。”[5]语气里充盈着在不同系统间穿梭和不被规则驯服的自得。要想成事,创业者得从各处借力。各套服装、一身斑驳,恰是本土颜色。当时,这里还有一些希望,希望中国的暧昧不清、鱼龙混杂的方式有朝一日可以替代西方那个干干净净、恒久不变的系统。

遵义国际策展会议,“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策划项目组成部分,2002年
图片致谢长征计划
恍惚中,我听见论坛现场的一位画廊主说,她实践的新颖之处在于结合了市场和研究、实践和理论,画廊并不屈服于某一个领域的规则。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十几年的两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我太年轻了,并没到过那个现场)。我忍不住想,是否因为太迅速地成功,曾经的“替代”生态才没有变成今天普遍的知识和语言。2008年之后,当长征恰到好处的反叛令人困惑时,长征空间渐渐变为正经的商业画廊,策划、研究和实验项目划入了长征计划。四不像收束成“画廊”与“机构”两副干净面孔,鱼龙混杂潜入水面。在这次论坛里,有艺术家创办的想像力学实验室、疫情爆发后上海出现的“栏杆外”和33ml off space、时代美术馆的外延项目媒体实验室和社区实验室、展览讲座留学咨询兼顾的“副本”……这场论坛的介绍把“机构‘“打上了引号来表明论坛召集的实践与典型机构的不同,表明着这次相聚缘于一种否定,即它们都在逃离典型的白盒子美术馆。
可正像梁中蓝反问的,干净、整洁、稳固的“机构”几乎只存在于观念当中。从泥泞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事物,哪个不需要找到自己的谋生之法和叙事?回国后,我脑海中反复重播的一次有关“机构”的对话,是一位刚刚认识的年轻朋友说她自己“在机构工作”。当时我亢奋地追问,想跟她讨论“机构批判”在国内的水土不服。她略带尴尬地解释,并不是美术馆或者基金会,而是留学咨询机构。我当时的错愕证明,水土不服的恰恰是我,脑海里只装着一种“机构”的定义。
如果,不,是既然,既然这片土地上有各式各样的机构,那么“替代”究竟指的是什么?即便不踏入“机构”和“替代”的非此即彼,这些论坛里的实践仍然有其自称——公司、空间、画廊、杂志、工作室、平台、社区、团体、组织、俱乐部……对这些事物来说,美术馆或者纯净的”机构“在它们的视野里吗,是它们的对立面吗?如果不事先施加一个”替代“,这些实践会如何认识和描述自身?是否还会存在一个共同的称谓,即“我们”?
与我无关
2015年,我刚刚到伦敦,在策展系读硕士。第二个月,我跟马来西亚的同学Zena搭档讲策展人奧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的一篇文章,《后殖民星座》(“The Postcolonial Constellation: Contemporary Art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Transition”)[6]。从北京移居伦敦,我的身份认同从山东人变成了中国人。Zena抛出的橄榄枝被我解读为亚洲内部的亲密。为了这次课堂展示,Zena带我远程采访了马来西亚艺术家舒希·苏莱曼(Shooshie Sulaiman)。舒希身上的马来西亚和华人血缘又让我以为,因为舒希,我便可以与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的英日殖民历史相接,也算间接搭上了课程题目里的“后殖民”。课上临近讲演结束,老师突然转向我,问我“你在中国的后殖民经验是什么?”(“What is your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in China?”)那个问题让我困惑——我,后殖民,和中国?这问题如同把我扔到了北京晚高峰时的地铁车厢里,被挤到双脚悬浮,落了眼镜。我的嘴张开又闭上。我在中国怎么会有后殖民经验呢?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早就被毛泽东赶走了。要有什么“后”的经验,难道不是后社会主义?
那刻的失语一直在我身体里徘徊。为什么一位英国策展人会认为我有“后殖民”经验,为什么我以为“后殖民”在亚洲之内、中国之外。一开始,我当然会觉得问题施加于我就有暴力:虽然后殖民反对均质化的西方、单一叙述的艺术史,但我的生命经验是否也被“后殖民”这个词语冠名并且均质化了?可是我也并不觉得老师是居高临下地发问。他不是位赶时髦的理论家,做了印度手工艺的研究很多年。“后殖民”对他来说更近乎通往西方之外的无数甬道之一。
这之后,或许是因为我时不时在Youtube上听对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晦涩文章的讲解,或许因为我终于有了些流民经验,渐渐地,我终于在“后殖民”的时空错置、叙事破碎、残暴横生、无可言说里读到了自己。不止印度有这些,不止英国这个前殖民帝国有这些。在被称为“(后)社会主义”的现实里,也有这些。这是我自己被重述的阅读过程,或者说,是我逐渐理解了使用不同词汇的人的意图(intension)。这似乎比读懂斯皮瓦克来说更为重要。后殖民、去殖民要撼动知识和常识的构建方式,让穷困之人意识到自己已拥有隐秘的知识、创造了独特世界。这种对认知正义的追求,常让我想,那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可以和“后殖民”碰面、理解对方?第三世界没有共享同一段历史,全球南方只是一个相对位置。而不同现场之间的倾轧和反抗,若要彼此理解,也需要仰赖翻译,有时候是理解对方在具体经历什么,为什么要说话。
2008年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叫“与后殖民说再见”。标题如此直接,几乎是大陆当代艺术界最“从中国出发”回应国际议题的一次尝试:它点出1990年代开始中国艺术家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怨怼,也把生长在大陆的人们(如我)与后殖民话语缺乏情感与认知联系的情形挑到明面。那届庞大的三年展并未花费太多力气向大陆的艺术工作者解析“后殖民”这一词语、流派、学科,或者讨论它为何会成功、为何中国会不在其中。三年展的真正靶子是国际当代艺术系统中的话语权力。主策展人高士明说,“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给当代艺术界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艺术的政治化”。[7] 这些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使自己陷入一种机械、呆板的‘漫无边际的政治正确性’,后果是“将当代艺术空间置于一种审查之下”。[8]“审查”指的是国际当代艺术界让政治和社会议题先行。
那么,要号召一种去政治化的艺术吗?三年展强调自己并非要淘汰“后殖民”,而是希望刷新和挖掘诸如“身份”和“他者”这些已经僵化的观念的可能性。但如何挖掘、如何做到三年展的另一个口号“从亚洲出发”?三年展调用的仍然是惯常的工具箱——展览、放映会、画册、委派创作,在不同地点召集研讨、编纂读本、邀请艺术家和哲学家加入。规模当然庞大,野心也十足。但如果以“后殖民”为议题的西方双年展和文献展没有让中国艺术家们生出参与感,那么运用相似方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能否让中国艺术家和大陆之外的参与者转变?这届三年展示例了“中国作为问题”,却没有“自己作为方法”:人们尚未冒着可能犯错的风险开始谈论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尚未阅读人的具体经历和体验。否则,阅读斯皮瓦克谈到的“庶民”(subaltern)的不可见性,一定能让策展人和艺术家们走出三年展,想起中国的女性、乡村、农民工和底层人。说到底,“向后殖民说再见”仍然是艺术系统内部的问题,甚至是别人的的问题。
我和“后殖民”最后和解,是因为2019年底读到了一份资料。拉希德‧阿拉因(Rasheed Araeen)在1980年代创办了Black Umbrella,为在英国生活的非白人艺术家举办展览、建立档案、出版画册。我意外发现拉希德所说的“Black”不仅仅是今天意义中的黑人,而是包括了所有非白人:来自亚洲、非洲、加勒比的人们,所有混血的、在西方社会被遮蔽和遗忘了的人……要按这样的定义,我也是黑人。这个震惊一直跟着我。半年以后,2020年的初夏,我在伦敦跟随Black Lives Matter游行队伍前进时,心里念叨着这句话:我也是黑色的。四周深深浅浅的肤色一同列队前涌,人们敲锣打鼓、齐声歌唱,喊出口号、伸出用亚马逊箱子临时改装成的宣传牌。英国的第一轮封城当时已经过去了,游行里鲜少人戴口罩。但我胆小,还穿着透明雨衣、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每当有人狐疑地看着我,我会凑近ta,轻声说,“yeah, I am Asian, and I feel black.”
身形
吴山专曾经出过一本小说《今天下午停水》,是本时空被折叠、穿刺,场景漫漶的自传。但叙述者似乎并不迷狂。场景里总有确凿的细节,尤其是汉字的排列,锱铢必较。对话和字句甚至因为过于确凿而开始分裂、增生、杂交。在某个时刻,字句掌管了生活,犹如天神律令———
“今天下午停水”对人是有涵(含)义的。还在小的时候,我与我同年龄的小孩一样,肩膀上就有了红肿的烙印(不是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扛枪后的烙印)。
我有理由想念那根扁担和那两个木桶。扁担上写着“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木桶上写着(防水的)”打到xxx年月日“(别的地方发生什么)。我不但为自己家挑水,还为“五保户”张大娘挑水,响应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全国运动。
那时,夏天的水龙头是上锁的。[9]
现成物曾构成杜尚的现实。从这本小说来看,对吴山专来说,现成物远远比不上“现成字”威力巨大。现成字并不一定需要在游行中通过被喊成口号才能进入人的肉身。作为通知、证明和标语的现成字,创造真实、消灭欲望,在人类的生活里逐渐背离意义、成为形式。[10]吴山专和朋友们在1986年做的那场展览《75%红 20%黑 5%白》里布满了字,犹如一片猩红中散落的义肢。吴山专在被红底黑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空,目视镜头、与字互文。他创造伪字和赤字,让字不可表意,但谁能说这些字不是幸运儿?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标语、80年代“读书热”里的西方哲学翻译、90年代市场经济里的的广告和合同里,字始终承受着意义的独裁。字和人和物,都因形式而被利用,身不由己。要获得自由,必须先从这一身形中逃出。

吴山专,《今天下午停水》 (又名:《大字报 紅色幽默系列 赤字 — 长篇小說<今天下午停水>第二章若干自然段》),1986年
装置,墨彩及广告彩、宣纸,约3.5 x 4 x 6 米
图片致谢艺术家、费大为档案及亚洲文献库
沈莘的作品《四条道》(Four Tracks)里,四组不同时空的中国铁道工人遭遇了彼此。ta们开口说话了,因为自己的队伍里有人死去、有人消失,不知道是哪队人带来了灾厄。《四条道》是一场三幕剧,但脱离了任何具体人物和场景,没有种族、肤色、年龄、体态的线索,观众仅仅能在屏幕上阅读句子。每句话从一片纯色的背景上浮现。点击屏幕,背景变色、句子消失。有时,要屏幕变色几次,沉默一会儿,新的语句才又出现。
色彩轮换中,破碎的对话行进着。读者可以拼凑出这里的中国工人(Chinese)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奥罗比亚(Oromia)、美国的内华达和犹他州、新疆的库尔勒和喀什———或许ta们是如今正在非洲经济援助的中国工人,1860年代在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人移民,1974年修建南疆铁路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当地回民。[11]这个莫名其妙的空间因众人的聚集而变化着样貌,如坠迷梦的人们不断区分着“你们”和“我们”。ta们讲的中文的台词简单又拗口,有时带着错别字,让人想起不同地方的人说中文时的不同口气:
“泛亚洲铁路是我们的时代遗留给你们的礼物
……
但你们更贪心啊,盯着比人的土地,占为己有时也没看出什么羞耻惭愧
……
我们跟白人殖民地的出发点是平等的啊
……
也可以说是我们失败了
……
咱们应该继续找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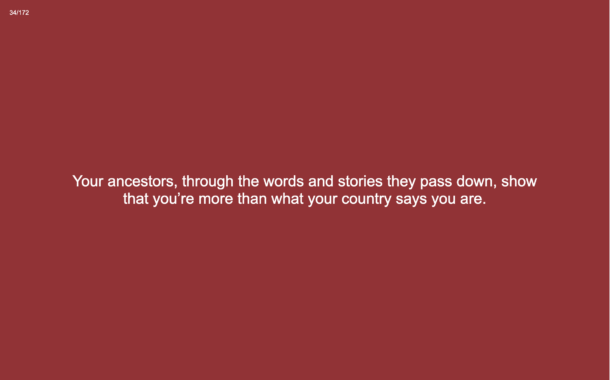

沈莘,《四条道》(截图),2021年
《四条道》由广州时代美术馆委任制作,首次发表于美术馆期刊第二期《亲密星图》(2021年4月)
图片致谢艺术家与广州时代美术馆
对话并不连贯,或许是被风吞噬了。沈莘把剧场削减至零落的语句,把一个角色削减至一块颜色。在语气、口音、停顿一起被抽象后,语言的暴力和局限,人对语言的巨大依赖与这一依赖带来的陷阱也暴露了出来。沈莘并没有再与某个词语或者身份纠缠,而是借“对话”这一文体暴露出人们之间流动的误解与理解。在这片迷蒙的风土中,不同的身份和语言逐渐污染了彼此,如同色块在变幻中成为一片光斑。

鸥飞鸿,上海推手活动的招贴(人在哪儿,哪儿就有推手),2022年
2022年的春天,我从小区围栏中一个狭窄的缝隙侧身钻出、逃离了上海。到了六月,广州已经炙热如烤,但我借住的房东绵绵一定要拉我和同伴去晓港公园。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一群年轻人,汗衫、瑜伽服和长裙交错着。没什么人聊天,也没人刻意沉默。几个人闭着眼睛、左右转身、晃动着像新鲜面条一样垂下的双臂。有人说一声,“我跟你推吧!”,就面对面靠近、双脚前后分开、膝盖互抵,然后两人的胳膊粘连、旋转着,试图让对方失去平衡、脚步离地……这是高压俱乐部组织的练功,说是俱乐部,但不需要拜师或者引荐人,谁都可以来这里松肩、松身和推手。在屡屡被推出我和对方组成的圆形、又总被拉住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几个月来最轻松的与人相处的场景。一个人的衣着、外形、样貌在这个过程里,变得太过微不足道。搭上胳膊与手臂,闭眼。重要的是倾听对方内在的力量,要往哪里去,在哪儿消失了。名字可以是假的,但身体真实。忍不住讲话时,我们说的是“啊?”“哎呀,我要倒了!”“嘿嘿”。语言被拉回此时此刻,我在失去平衡、却也被伸手拉住。我们的形状在一起变化。我们在一起变形。
在《四条道》的最后一幕里,灾厄尚未消除,但沈莘藏了一句与何去何从无关的解救法:真诚遭遇时,你我在眼神中看到彼此的痛苦(In a sincere encounter, you meet each other’s pain in the eyes)。当话语不合、无法起效时,你和我仍然分享着此时此刻。最后的对话里,人们不再使用宏大的词汇,开始分享对方的食物,异域的水果和香料进入了肠胃。肚子变圆了,身体的地貌在悄悄改变。
“我”和我的语言都不是固定的,正像我的肚皮和梦境。
[1] [日] 和计哲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pp. 123-27。最早出版:《風土——人間学的考察》(东京:岩波书店,1935)。
[2] 雷电所公众号的最新推送中仍然定义为“非营利的艺术机构”。《雷电,OK! AR虛拟首饰内测邀请》,https://mp. weixin.qg.com/s/WtKm59JEUOwC-MEFROgeXw, 2022年11月11日。
[3] Merriam-Webster 辞典中对 institute 的定义是“an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 cause;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especially one devoted to technical fields; a usually brief intensive course of instruction on selected topics relating to a particular field…..”
[4] 原文为 “Longmarch space is not so much a gallery as a center, a base, and a work station that looks to connect the art world with Chinese society, and to connect China with the world. The space functions as a “curatorial labora-tory” dedicated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ating, display and artistic crea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discourse, between objects and text, and between audience and artists.” ‘Homepage’, 25000 Cultural Transmission Center, 2005 <https://web.archive.org/ web/20051129031831/http:// www.longmarchspace.com/ english/homepage.htm> [accessed 17 November 2022].中文由笔者翻译。
[5] 叶滢,《窑变798》(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p.72。
[6] Okwui Enwezor, ‘The Postcolonial Constellation: Contemporary Art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Transi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4.4 (2003), pp. 57-82.
[7] 高士明,《“后殖民之后”的观察和预感》,《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王璜生、高士明、Sarat Maharaj、张颂仁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2008) , pp. 44-51.
[8] 《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度》,《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王璜生、高士明、Sarat Maharaj、张领仁 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p.15
[9] 吴山专 国际红色幽默,《今天下午停水》 (2008), pp.9-10。
[10] “真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学到的。请多读报纸。我把报纸上讲的和我周围的环境做一比较,认识到报上讲的是‘真实的’。后来才知道这—“真实’是建立在,消灭掉任何别的可以是真实的人的欲望的基础上的。”《今天下午停水》 (2008),p.211-212。
[11] 沈莘与笔者的邮件,2022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