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幕:三种关 抽象艺术的美学想象
| 2012年02月0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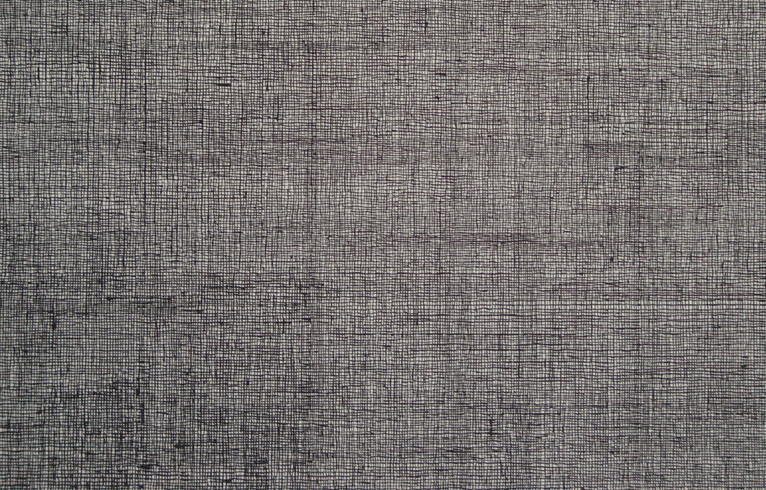
『竹幕』1 是一个意识形态术语,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起。用『竹幕』来描绘21世纪以来中国的抽象艺术,正是为了说明国内的抽象艺术实践不仅仅是一场宏大的文化建构,也具有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呈现为自发的和在传统内部进行的。
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会以对待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今天国内的抽象主义。二战后,美国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成功而彻底地改造了欧洲的传统现代主义,并进而确立了自身的文化中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国内的抽象主义具有类似的目标。然而,今天的语境对这种艺术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为什么绘画作为一种普遍没落的艺术门类在西方当代艺术语境中逐渐式微,而中国的艺术实践者们却仍旧满怀信心地选择抽象艺术来构建自身的文化景观?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构成一种有效的文化建构手段,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了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抽象艺术在全球艺术格局中的政治处境,还有一个与“竹幕”共生、并更为人熟知的概念“铁幕”可以作为参照。与这个保持了40余年稳定状态的术语不同,竹幕的内部显得模糊、不稳定和游离,它正好反映出东方民族国家在建构自身政治、社会、文化主体时的内敛性格。在今天,主流的当代艺术实践恰好可以形象地对应于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状态,并呈现为两种“东西方”问题的探讨。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初铁幕的消除,“东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俄罗斯、东欧和德国展开深入的讨论,当下艺术实践所呈现出的政治化面孔也多得源于铁幕解除后被释放的巨大开放性、创造性与包容性;而在另一方面,“东西方”作为一种文化和美学建构,为了突出自身的地缘性和主体性,这种实践又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竹幕”状态。对于21世纪以来的中国抽象艺术实践,这种状态表现出的内部不稳定、不统一,相对滞后和保守等显征,则可以反映出十年来这种宏大建构的另一张面孔。
今天,如果我们力图为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中国抽象艺术做一个概观式的描述,就无法回避以四次展览作为标志性事件来建立这样的文化视野。它们是2003年分别由批评家高名潞、栗宪庭完成的“中国极多主义”展、“念珠与笔触”展,2009年高名潞策划的“意派—世纪思维”展以及2010年由意大利批评家、策展人阿基尔·波尼托·奥利瓦策划的“伟大的天上的抽象”展。作为三种不同的美学理论产物,这几次展览的标志意义在于,它们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对抽象艺术做了宏大的建构。如果说整个1980年代、1990年代的抽象艺术是在西方艺术史逻辑或国内“本土化/民族化”理论框架下,对艺术形式、构成以及材料进行的现代主义探索,那么以上几个展览则说明艺术语言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开始得到自觉地反思,从而使得当下的抽象艺术具备了进入当代艺术语境的可能。同样,2003年后,越来越多的声音预感到国内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抽象艺术,其复兴之日指日可待,2010年奥利瓦的展览是此类呼声的一个高点。我们也很难将这种种呼声视为以上展览共同诉求之外的产物。

可以说,基于同样的表述对象和目标,这三种理论及实践以不同的理论格局和视角对抽象艺术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挖掘、整合。因此,讨论这几种理论内部所呈现的差异性及共通性,无疑将成为考察这一个时期抽象艺术整体状况的一种内在要求。相应地,两个对中国当下当代艺术实践至关重要的问题将得到初步的回答。第一,当中国力图从传统中挖掘资源来建构其“中国性”,而抽象艺术又构成这样一种潜能时,传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注入到抽象艺术这种西方艺术语言中的?第二,这几种理论的建构背后是否具有某种思维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将反映出第一代、第二代中国现当代艺术推动者们的整体理论气质?
从2003年的“中国极多主义”展览开始,我们首先发现,批评家高名潞并没有将整个展览放在抽象艺术的系谱中讨论。这个展览的外延很广,包括邢丹文、邱志杰、顾德鑫等摄影、观念、装置、行为艺术家都被容纳进来。更准确地说,这次展览是基于被改造的抽象主义精神之上一次更广泛的文化实践。为了对西方语境中的抽象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造,高名潞将以重复、体验、书写式的观念性创作过程引入抽象主义概念中,并引申到中国禅学的哲学层面;同时,为了在现当代艺术内部获得一种逻辑上的传承性,他又将这种“极多主义”视为前卫运动时期“理性绘画”的延续。可以说,禅宗式的东方体验与西方理性主义两种本质不同的理论被整合到“极多主义”之中。这与批评家本人用“整一性”来阐释具有独特中国情境的现当代艺术的逻辑是吻合的。在随后由批评家发展出来的“意派”理论里,这种意图变得更加清晰。
从本质上看,“极多主义”或“意派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框架中的,也是以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一路“意境说”的当代转化。栗宪庭于同年在“念珠与笔触”展上形成的理论格局就很不一样。这个展览以抽象艺术为唯一讨论对象,而不是首先预设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虽然我们对用禅宗的精神来进行理论架构的方式有不少质疑,但栗宪庭在两个层面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审视抽象艺术的角度。第一,他以一种通俗直白且非常中国化的语言写作,并用中国传统手工劳动的繁复性这一要素为艺术作品建立意义,这显示出批评家力图完全抛开西方抽象主义的分析模式,从而在艺术作品和理论内部彰显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第二,栗宪庭的理论最终谈的是精神,如他频繁提及心灵的“治疗”、“修性”、“平复”等词语,将中国传统引向一个哲学、宗教式的精神问题,这就突破了20世纪以降以笔墨、意境、形式和美来谈论东西方问题的主流美学传统,开辟了另一种对待传统的新角度。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高名潞和栗宪庭的理论都力图为抽象艺术建构一套具有强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阐释体系,这是他们差异性背后的共同追求。不过,尽管两位批评家总是极力避免落入西方阐释话语的窠臼,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现代主义,尤其是二元划分的思维模式还是影响了他们。栗宪庭提出“极繁主义”是在他1999年对美国极少主义进行了半年考察后慢慢成形的,而他用过程性、手工性等观念色彩很强的元素来阐释艺术作品,不能没有极少主义理论模式的影响。有趣而费解的是,栗宪庭引用中国传统的女性文化如纳鞋底、绣袜垫来比喻他的极繁主义,还赋予西方极少主义一种男性色彩,这就无形中使得东西方文化获得了某种隐喻。同样,尽管力图用“整一性”来阐释中国的现当代艺术,高名潞的理论还是明显地假想和设置了其对立目标: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背后的一整套理论传统。

不夸张地说,当批评家力图勾勒一个想象的“敌人”时,他所要构筑的主体其实也就已经显现了。只不过,如果这种想象是在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框架中完成,这种美学性的想象就只能为全球文化编造好看的景观,而不是构建具有能动性的文化主体。2010年,奥利瓦的“伟大的天上的抽象”展就代表了这种美学想象的高点。其展览文章中不断以马可·波罗式的口吻来惊叹中国的伟大哲学观,这种态度使人想起那些在竹幕时期被邀请来华的西方人,如毕加索、斯宾塞,政府报道一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种自以为是的热情在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尽管奥利瓦用“健康的消极乌托邦”准确指出中国抽象主义的相对保守位置,从而为艺术家的个体创造留出了充分的位置,但他却过于乐观乃至夸张地赋予这种艺术某种解放价值。他的理论大致做了两个事情,一个是生硬地用自己1970年代的“文化游牧”理论讨论中国抽象艺术,似乎这样,抽象艺术就获得了一种针对前卫本身的批判精神;另一个则是一边延续高名潞或栗宪庭的观点,注入并强化了东方的自然论、整体观和唯灵论,一边突出西方的科技主义、逻各斯主义,使得东西方一词作为对立和隔绝的概念更加突出了。
奥利瓦作为一个被邀请来的批评家策划“伟大的天上的抽象”展览,这样的身份与15年前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主动推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而对于奥利瓦的个人阐释,国内有些批评家、理论家不假思索地将这种视角升华为西方的普遍视角,这说明我们也仍然存在着一个鲜明的西方概念,因为奥利瓦的个人视角并不全然是西方的。
在静态的美学框架下谈论抽象艺术必然局限重重。高名潞、栗宪庭、奥利瓦三位重要批评家的理论是21世纪头十年里最重要但不是全部的理论建构,成气候的还有实验水墨,民族性及宣言性很强的“第三种抽象”,在学院内部则是以现代主义为基调来探讨抽象。这个时期抽象艺术的面貌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无论以什么方式呈现,它们都体现为一种内部的和民族性的探索,因为这种探索最初及最终的目标都是基于一种宏大的文化意识,而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文化主体性的想象,这种实践好像总是被一道幕墙隔离在“内外”之间。困惑的是,当我们谈起建构一种独立的多元文化时,也很少有人能准确回答,这一道幕墙是该拆毁还是应当受到保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道幕墙首先应该是能动的,柔软的,也是可视的。只有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才是一个自信的主体和开放的主体。
1 1949年3月14日,在中共中央刚刚结束西柏坡会议准备进城赶考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就以西方的偏见写道,北平的共产党头头们已经降下一道竹幕,北平将与世界彻底隔绝。“竹幕”一词应运而生,并成为今后半个世纪里西方指称北起朝鲜、中国,南至越南、老挝这片广大区域所形成的一个模糊的政治共同体常用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