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蜃楼
| 2016年01月06日
我刚结束了一个半月充斥着展览、读物和派对的欧洲之旅,回到我洛杉矶的家。再两个月前,我向交往了四年的艺术家女友瑞秋·拉拜求了婚。自己似乎很长时间没动笔写散文或短篇了。
数月前,岳鸿飞邀我为即将出版的一期《艺术界》写稿,什么都行。我说得过一阵。他说没问题。几周后,我告诉他,我想跟朋友,英国艺术家艾德·弗尼勒斯一同去拉斯维加斯过7月4号独立日,之后会写个游记。
……接上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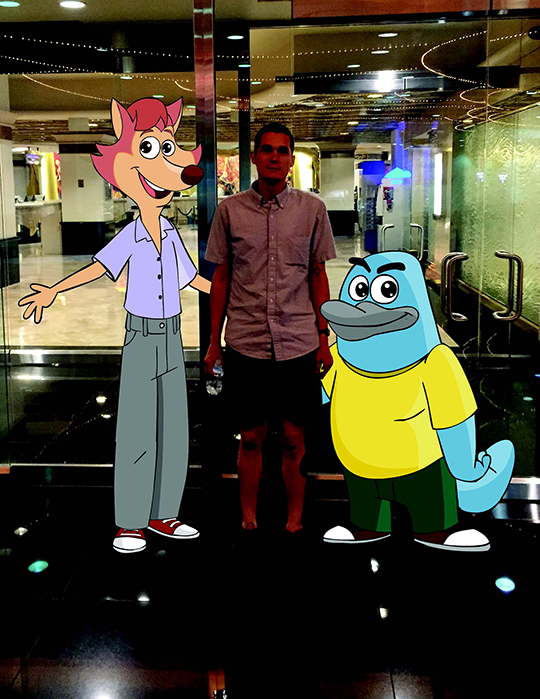
那人给他亮了亮自己正在抽的烟,随后又对着我们咕哝了几句。艾德说,“抱歉,我听不懂你说的。”那哥们抬高嗓音大声重复了一遍,“你们都嗑不嗑可卡因?”艾德说,“噢不,谢谢,晚安。”
我们从酒吧告别了这位温柔硬汉后就四处溜达,最后到了一处艾伦·德杰尼勒斯主题的自动贩卖机旁,开始聊起女人和关系的话题。过了一会儿,一帮安保人员在附近聚集起来。艾德疑神疑鬼。我觉得大概只是巧合。艾德不信,于是我们就起身再次转悠起来。我们溜进了一个新的房间,艾德想换张桌子坐。但艾德不想玩21点。他只是想交际。他在一场5分钟的谈话(不是赌局)里输掉了40美金之后,我决定我们应该换个地方去交际。之后,艾德赞同眼下应该由我攥紧我们赢得的全部的钱。
艾德说,“咱们找个酒吧,应该不难。”我们闲逛了似乎很长的时间,试图弄清楚出口在哪儿。最后,艾德问了两名年长的亚洲女人(实际上她们是年轻的白人女性,金发,穿着露露柠檬的衣服,喝着星巴克的冰咖啡)怎么从赌场出去,她们往前一指。
我有几个小时没看表或者手机了,这时我意识到外面天已经大亮。等我们进到光(和热)里,我的腿不再能支撑住我了。我跟艾德说我得回酒店。他说,“抱歉,我不能那么做。我现在感觉太好了。这种感觉会持续很久。”我问,“你确定?你会没事儿?”他说,“没错,只要给我足够的钱买酒买烟我就没事儿。”我给了他20块钱,然后我们抱了估计过分长的时间。我清楚这一点是因为在我走向出租车的时候旁边有个抽烟的男人朝我眨了眨眼。
我又上了另一辆车,这位司机想聊天。他想跟我聊天气牛排馆和当的哥的事儿。可这会儿除了艾德我跟谁也没法聊,于是就没应声。

一碰到床,我的腿感觉就好了起来。我的整个身体感觉都好了起来。我闭上眼,开始快速从各种念头里过滤要写什么,要怎么处理这个故事,抑或这场旅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堆杂念中筛了约莫一两个小时之后,我的脑袋就变得和身体一样疲惫了,我开始迷糊。我为能睡上一会儿兴奋不已。结果这时,我的电话嗡嗡响起来。艾德在给我和迪恩群发短信。
“致幻好厉害”
“我的胳膊像爬虫”
“键盘在发光”
“光是坐在这儿”
“不想被现实感插进来”
“虽然我知道那就是个东西而已”
“在二维空间感觉真怪”
“我坐在山顶的长椅上”
每次快睡着的时候,我就会看见塞壬。一开始,我警觉到这是某种预兆,艾德会被抓起来或是怎样。然后,我看见一辆救护车,我开始害怕一旦自己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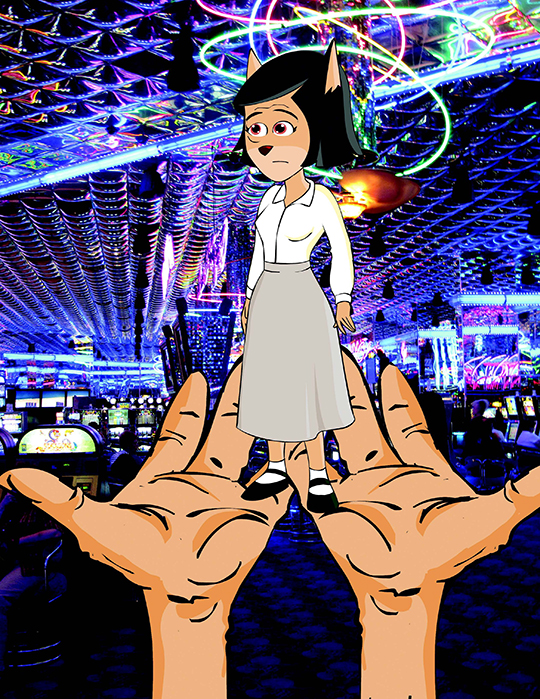
在床上躺着,用iPhone看医疗服务的应用WebMD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确信了自己哪儿不太对劲。我的心怦怦跳,胃就像打了结,左边胳膊现在是麻的,疼痛一阵阵闪过。我犯心脏病了。最终我决定弄醒迪恩,告诉他我心脏病发作了。迪恩让我放心说我只不过是惊恐发作了,他说我估计就是在担心艾德。我觉得也是,于是就冷静下来一点儿,我谢了迪恩几次。
我打开电子邮箱,收到了阿玛莉娅的这封信:
希望你们的乐子配得上我的眼泪
你个混蛋
阿玛莉娅·乌曼
7月4日
我笑出了声,然后就想起前个晚上我们仨看到霓虹灯在视野里融化。我想起戴夫·希基。他搬去维加斯后就对那儿上瘾了,对这座城市的描述从里到外都是美妙,但我一向保持怀疑。他是真爱上了这座城,还是只是博噱头?有谁真相信他们所说的吗,还是说每个人都只是在装成别的人?
像戴夫·希基这样的人最终扮演起了偶像领袖的角色。他们最终有了膜拜者要去领导;或者至少至少,他们有了狂热的追随者。戴夫讲话充满激情,写作充满激情,人们对他很是狂热。
我注意到了,艾德和他有某种相似之处。不过他没有戴夫·希基身上那么多宗教狂热的成分。艾德更有条理。艾德更狡猾。艾德更有锐气。艾德还非常的英国,而戴夫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牛仔的漫画版自画像。他们都格外地迷人、有魅力,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戴夫会被看作天才并被授予50万美金作为对他天赋的回报,而艾德则被各机构全权代理以便举办大规模展览。我对这两个人都表示支持。
不过,戴夫教派和艾德教派有一点特别显著的不同。戴夫明确声明终其职业生涯他都是反体制者。艾德则不然,他敞开双臂拥抱企业界以及名流的生活方式。他的全部项目皆由电视上的情景喜剧和真人秀节目以及社交媒体而来。有十年的时间,他的约会对象正是近来在某部大范围发行且广受好评的电影里饰演斯蒂芬·霍金的太太的演员。

最近我一直在想,大概我们这代人普遍认为,最好的颠覆方式便是参与其中。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见识了戴夫·希基之辈的摇滚明星朋友们最终都变成了瘾君子或背叛者呢?话外音:这是否就是他几次三番退出艺术界的原因?或许吧。或许,我们同代人中的那些人之所以以颠覆式行为参与其中,是因为我们是听着“暴力反抗体制”乐队长大的?这么说来我们是否要问:“他们那会儿要反抗的体制归根结底是什么?”这个乐队出的专辑里头含有关于革命的歌曲,而发行这些专辑的是主流厂牌“史诗唱片”——这也是他们从职业生涯伊始便签约的厂牌。可就连我也抱有这样有罪的态度:“是啊,可谁不是和‘暴力’搅和在一起呢?”
如果说新式革命的重点便是将你的消息发送给尽可能多的人,那么“暴力反抗机制”便树立了一个相当坚实的榜样。可如果扎克·德·拉·罗查和汤姆·莫雷罗但凡曾有意对他们那代人产生更大影响,而不只是引述一段迈克尔·摩尔的原话,那么他们就不该雇他来给他们导演一部土得掉渣的音乐视频。假如一位艺术家的目的是让人们真正地去改变想法或改变感受——这也是我认为应当有的样子,那么他或她或许就不该追求变得像(社交媒体明星)“胖胖的犹太人”那样。
我得说,艾德正在做一件令人折服的工作——在文化和经济方面提出新鲜的洞见,超越社交媒体“热推”的表面价值——尽管他也定期利用社交媒体来做这些。更特别的是,他满怀好奇地投入时间,研究中美洲人所关注之物的复杂而矛盾的本质,以及这些事物如何在诸如好莱坞和伦敦的其他地方显现出来。艾德最新的作品对社会循环及反馈回路提出了质疑,或者说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身处艺术工业和娱乐工业的那些人在试图反思文化峰谷的时候,宁愿制造自然灾害也不愿接受常规的季节性天气,这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他们试图打乱一个“美国凡人”的经验(这是他们从《人人都爱雷蒙德》一剧的成功当中学来的),代之以“后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各种不温不火淡然接纳的事例——已婚同志伴侣带着领养的越南女儿,不具威胁的黑人邻居,粗俗的拉美人,平淡无奇的艾尔·邦迪(现实中正由饰演过艾尔·邦迪的演员艾德·奥尼尔扮演着)——以便制作一出能够吸引无处不在的“温和、明理”的人民的连续剧。可这种闹剧般被迫发生的合并杂糅是否就是想象中的理想情境?《摩登家庭》是否哪怕在极小程度上象征了某种当代经验?并不是。很可能没有。但若回到极端保守的1950年代,露茜·里卡尔多和瑞奇·里卡尔多也并没有。可他们好玩儿,他们给人带去希望。抛开艾德作品中某些凶险、恶声恶气的层面不说,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要来点儿好玩儿的,并给人以希望。这一点有悖于人们通常所习得或以为的艺术家的角色、职责,而我,无论现在将来,都强烈地拥护这一点,把它看作是艺术的积极层面。
从拉斯韦加斯回来后,我就开始看《镜花水月》(又名《真实之虚》)。这是Lifetime电视台新出的一部剧集,讲的是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幕后真实。原型是一位毕业后做制片人的年轻女人的故事。主人公瑞秋的很多方面都让我想到艾德。她经常做些很可质疑的事情——这些事情仿佛是她周围的人想要任她去做的,这些事情似乎是为了制造实实在在的娱乐——而我像大多数这个节目的观众一样,和她享有共鸣,哪怕是在她同别人妥协的时候,而当她自愿允许自己妥协时,我无疑、显然更有共鸣。艾德也做妥协之事——令人惊讶的是,他很常做。我欣赏这种可供质疑的行动上的脆弱性,且我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和生命来进行这种妥协。对我来说,了解这种脆弱性实际上有多真实,远不如一开始就让人们体验到将一个人的自我置于这种脆弱地位意味着什么来得重要。
说到这儿,我接着问我自己,“这个新的Instagram化身项目怎么样?”在这场旅行之前、途中和之后,我试着问过艾德好几次这个问题。我的盘问不断得到某种经过排练的伪女性主义、后网络时代的长篇大论,说男人和女人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在线上吃得开。我个人觉得,他本来想要出版一本怪异的图像小说,这本小说首先会在社交媒体上运作,然后会在艺术市集上卖掉相应的墙上作品。这么做好像挺精明的,和真人秀电视节目制片人让参与者取笑彼此的方式大同小异。按两手方式去做。“按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受到版权保护的、注册了商标的品牌:艾德·弗尼勒斯。

或许那并非他想要的。但我也不觉得他想要的就是像“暴力反抗体制”或阿玛莉娅·乌曼那样工作。不过,问题仍旧在于:“谁不是和‘暴力反抗机器’搅和在一起呢?”我猜想现如今:“谁不是和阿玛莉娅·乌曼搅和在一起呢?”她是89后版本的天后碧昂丝,是一架显然对什么也不暴力反抗的机器。不过这架机器确实无疑协助了年轻艺术家将他们的讯息发送给尽可能多的人,或许有些时候,它还极尽高效地实现了这一点。
要知道,事物运行的方式是很有趣的。事实证明,迪恩前阵子决定为《i-D》杂志写一篇关于阿玛莉娅的文章。他说这很可能是他迄今为止写过的最为人知的一篇文章。我猜想,记者有时只不过是去到了最便于取得故事的地方而已。
而且,说真的,事物运行的方式同样是十分具有讽刺性的。事实证明,迪恩此外还决定,等我们结束旅行回去的时候,他要为《Spike》艺术季刊写一篇关于拉斯韦加斯的文章。他说这很可能是他迄今为止登上过的最美的出版物。我猜想,这位记者,他基本上就只去那些绝对是最便于取得故事的地方。那些也是迪恩所仰赖的后盾。
恶名是文化当中最炙手可热的吗?还是美?抑或是可相关性?或者是便捷?
在离开这座城市去往我们现在称之为家的地方的前一晚,我在我们的酒店房间里观看电影《独立日》,其间我用手机给自己写了一句笔记:“每个人都想做个人物。没有人想要诉说任何东西。”
我不认为这是必然真实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认为有任何可能了解到什么是真实。世界充满了海市蜃楼。艺术界对它们进行开发利用。这就是我们选择生活其中的世界——至少,对于艾德、迪恩还有我自己来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