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的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
| 2016年01月14日

上世纪90年初期中国文化界在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文精神”的论战时,出现了“现代主义的80年代”与“后现代主义的90年代”这样的历史断裂叙述。在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或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样的西方文化思潮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人展开了对自身文化与身份思辨性的探索。也许我们可以把并未发生在90年代的展览“大地魔术师”描述为一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公开宣战——当然,这又或是法国在文化上的焦虑,借此来挑战美国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先锋地位——正如策展人马尔丹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时其实缺少一场大型的、能够发人深省的展览去梳理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它所催生的新的艺术形式。此话所蕴含的“去西方中心化”或者艺术多元论的味道只是某种表面的措辞,真正的原因或许应该是利奥塔所指出的,西方现代性的元叙事存在着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993年,法国《世界报》的二月专号《辩论》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代艺术,画家还是骗子?”,报道了一场发生在法国的大论战。一方为当代艺术进行辩护,另一方质疑当代艺术意义。这场论战是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现代与后现代讨论的延宕。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作为佐证自己观点的“他者”:现代性实践要肯定和拓展自身,就必须不断地寻求作为实践对象的“他者”,而后现代也需要这样一个“他者”来颠覆传统现代主义通过否定“他者”来肯定自身的企图。
公元5世纪的时候,基督徒自称为“modernus”,文艺复兴时期,激进的思想家常称自己所处于的时代是所谓的“现代世界”,而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出现了“现代与古旧之间的纷争”,二战以后的西方社会,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降,又出现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大讨论。西方文化思想的推进依靠的是一条不完全以时间段为切割,而是以思想前后为标准的一种对“现代”的信仰。这些论争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除了比较新与旧的差别之外,双方都还会加入一个第三者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这时,所谓的“东方”常常会被拉进这场讨论里,成为论辩双方各自的论据。
80年代,中国的本土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西方对于现代化社会的定义,即:生产方式是工业生产,经济模式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政治体制朝向民主政体过渡——服膺现代主义大业尚未完成的欧洲思想界人士,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现代化本土性经验的样本;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却从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对集体信仰的批判与反思,对权威、中心或者传统意识形态的质疑与解构中,看到了旨趣相同的共鸣之声。可以说,近三十年来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中国当代艺术均被双方拿来做支持己方观点的重要依据:现代主义者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启蒙、理性、科学、进步、权利、主体性等现代议题上的共性,后现代主义者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解构、颠覆和消解各类话语霸权与中心主义上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在90年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再次作为第三方的“他者”被动地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当中。

这个时期的中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建设“现代化”,延续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思想脉络。因此中国的社会实践就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具体经验上提供了东亚版的支援。欧洲许多支绌于与后现代主义者辩论的启蒙思想辩护者,比如哈贝马斯等人,都很关注中国的实践经验。
但另一方面,参加“大地魔术师”展览的三位中国艺术家黄永砯、顾德新和杨诘苍。被认为保有高度的独立性,是中国最激进而无法被分类的艺术家。并且符合展览组织者对选择参展艺术家的标准,即:创作兼具普世精神和个人独特风格、不代表国家或民族——“大地魔术师”这样的展览是被放在后殖民理论之类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进行解读,甚至有研究者宣称,“大地魔术师”标志了西方现代性及其一整套意识形态、审美经典和制度体系霸权的终结。
自从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国际上相继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展览,荦荦大者有:1990年法国文化部资助费大为的“为了昨天的中国明天”、1991年费大为在日本福冈的“非常口”、1993年戴汉志等人在柏林世界文化宫的“中国前卫艺术”、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1993、1995、1997、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大卫·尼奥在牛津现代美术馆策划的“沉默力量”、1995年翰特在波恩美术馆的“中国!”等。
由岳恒、施岸笛及戴汉志在柏林世界文化宫的策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其实介绍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实际上涵盖了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前卫”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中国最新的文学、戏剧、电影及当代音乐和摇滚乐等。虽然在文献意义上超过了“大地魔术师”,但是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对西方当代艺术提出什么问题或者挑战。事实上,人们从这个展览里看到的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在踉踉跄跄地进行现代化尝试。

90年代在西方举行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最有趣味的是中国官方的身影,虽然姗姗来迟,但是已经有了一种“大外宣”的官方意识形态味道在里面。1997年中国官方选送威尼斯双年展的部分参展艺术家被官方视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言者和展示者,但却尴尬地被普遍认为与国际当代艺术严重脱节。
1999年和2001年,德国策展人塞曼连续担任两届策展人的威尼斯双年展,开始按照西方当代艺术的标准来挑选作品。他所邀请的艺术家几乎占据了全部参展艺术家的20%。但是这样强大的阵容并没有引发西方艺术界的强烈触动,倒是在意大利媒体的社会文化版面出现了通过中国参展作品分析中国社会变化的系列文章。尤其是2003年之后,威尼斯双年展上正式有了中国馆,许多被选送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里都能清晰地看到民族国家崛起的愿望。
另一方面,1998年张晴在温哥华策划的“江南·中国艺术展”、巫鸿策划的“瞬间——20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高名潞推出的“锐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虽然大都是典型的“私人叙事”,带有鲜明的波普主义特征,事实上却依然是在提供差异来重新构建自我诉求。
也就是说,虽然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常常以疏离反抗异化,以暧昧难解反抗集体的暴力和庸俗,并企图在材料与观念上寻求真正的解放。以波普主义的方法解构一切逻辑,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将审美主体“去主体性”,“去中心化”。这些发展特质得到推崇后现代主义者的欣赏,但又在另一方面,展现出一种以文化认同与族群共识为基础的主体性追索,同样让西方的现代主义者感觉吾道不孤——中国当代艺术正是这样以“他者”的身份,异常吊诡地同时进入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萨义德“漫游的理论”,即:一个理论或世界观在其发源地以外传播时,往往不仅其内涵被改变,而且还常常有可能被用于与该理论提出者的初衷毫不相干的其他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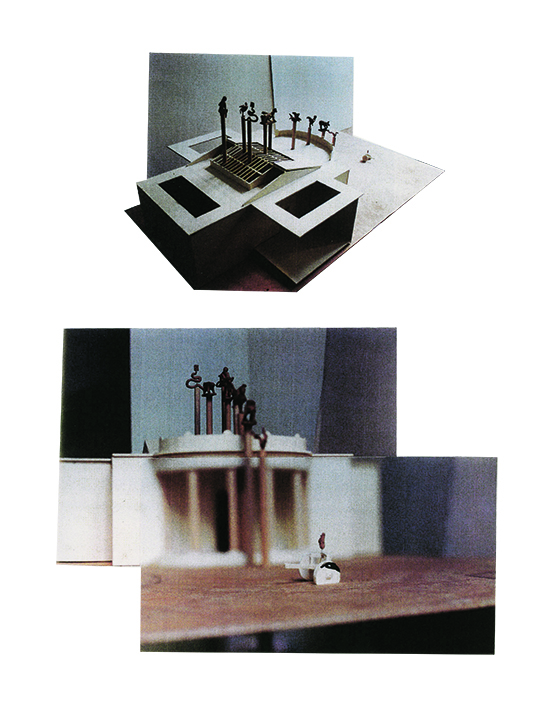
从一个比较深的层面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从80年代末、90年代受到的关注,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显然是上述的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嬗变。当然在接触到中国当代艺术后,欧洲又发现了许多本来已经在西方趋于平静的议题,在中国还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再加上中国社会实践里的所谓“本土性的现代化”,起了一个西方现代化的镜像作用,引起了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但是在21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趋于平静之后,随着语境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他者”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再重要。也许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回归真正的艺术问题本身有正面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