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观
| 2011年05月23日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教育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势必会演变为一场激烈的言语风暴,但它也极有可能又是一次泛泛之谈。因为艺术学院的教育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就像中国社会的其他问题一样深层与庞杂,无法在朝夕间豁然解决,而认识到这种局限才是着手解决问题的一个务实性前提。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八位从事(过)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其中既有从“清华”的美术学院辞职并引起热议的陈丹青,也有尚属教师新丁的杨福东,既有系科工作室的主持人,也有身肩系科、学校发展之责的领导者,他们无一不身牵美术学院具体的教学实验,也无一不在面对具体的教学现状。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殊途同归的改革路径,但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还是自上而下的拓展,他们的教育实践都无法摆脱学院领导的支持,事实证明,相比艺术教育的困境来说,一位兼具开放性与进取心的领导却常常是改革行动最有效的动力。而另一方面,他们讲述的教学实验只是局限在具体的系科建设上,并未触及现行的招考制度与教育体制,所以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学生问题,相比这些早年从艺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们,他们既要正视一批只是为了上大学的学生,也要平衡社会现实中日益增强的就业压力所施加在精英教育模式上的负面影响。而以上这些是“我的教育观”所隐去的相同话题,因为它会让美术学院的实验教学变成了一种事倍功半的努力。(孙冬冬)
吕胜中:
艺术更应该愉悦身心

1982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年画连环画系进修,后又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专习民间艺术,1987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现在美院一个新的专业——实验艺术系工作。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期间,我感觉最有价值的课程就是民间采风和考察。从传统文化里,我知道了艺术是什么,艺术不仅仅是绘画,还有许多别的形式,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有雕塑(或者叫做装置),有大地艺术,甚至有带有行为艺术特征的艺术形式,这和当代艺术的许多新形式没什么区别,只是没有被冠以当代艺术的名称。对民间艺术的深入了解让我在认识西方前卫艺术时一点障碍都没有,对我后来参与筹办实验艺术系也有很大帮助。如果没有这个铺垫一定有点遗憾。
在民间艺术系讲课时我开创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剪纸课”,我把剪纸当成与素描等同的造型训练,教给学生一种造型的法度。另外一门课是“造型原本”,在教学中发现我们教给学生的通常只是表面的样式,而不是形成民间艺术造型表象的原则,开设了这门课,试图从观察方法和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后来这门课不仅在民间艺术系,还在油画系、壁画系、雕塑系都上过,现在是我们实验艺术系的必修课,也是全国很多美术学院里都开设的一门课程。
1992年我第一次出国,在德国待了三个月,在那里受到的冲击特别大,当时我们的院校里培养的都是“画家”,我们只知道画家,不知道艺术工作的全面的概念,而艺术也不应该仅仅是愉悦视觉,更应该愉悦身心。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应该知道这些,回来以后很冲动,就想自己办学校。但我对经营一无所知,于是这个事情就作罢了,但我的脑子里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2004年时我参与筹备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大约经过一年的筹备时间,这个专业正式成立。我们的培养目标有两方面:一是使学生成为未来的主流艺术家和文化精英;二是能有从事社会工作的一般能力,也就是说能找饭碗吃。实验艺术系的本科现有16门专业必修课,共分三部分,一部分是造型基础,包括视觉方式、造型原本、色彩等;第二部分是艺术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方案课、思维转换课、文化艺术考察、公众审美调查等,第三部分是媒介形式语言,比如物质材料、影像艺术等。除了上面提到的造型原本,我还负责方案课。
实验艺术系能够建成现在这样,是我没想到的。在筹备阶段,我提交的筹备工作报告题为《勾画乌托邦》,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办学理念与方向根本不可能被批准,没想到交上去竟然通过了。在很多外人看来,学院是一个保守的地方,但是就中央美院来说,它的内部还是一个活水流通的地方,起码实验艺术办学的方案没有遭扼杀,在这里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现在大家对美术教育的批评很多,我觉得批评是容易的,怎样去做是很难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问题很多,问题多便需要解决,解决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所以难,但又不能停下来不做。
陈丹青:
艺术教育没什么好谈的

我从未“选择”当教师,但此生居然当过两回:第一次是1980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后,顺理成章留在油画系,任第一工作室助教,当时什么都没教,一年后就出国了;第二次是2000年清华美院袁运甫等老前辈希望我去,任绘画系老师,但连续四年根本招不到研究生,因为学生的英语考试通不过,所以后来我辞去了教职。
我从来不关心教学目标,也不记得具体的课程。我是野路子学画出身,从来不遵循什么课程。我在清华美院负责教学生画画,不过就是弄个模特儿画画,和所有老师一样。我不清楚中国的美院系统有什么特点,大概就是一天到晚填表格,排课程,开会扯淡,谈什么教学目标之类。我在清华期间,各届学生的总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很茫然,垂头丧气,跟着教条走。
在我第一次教师生涯中,我只是系里的青年老师,负责跑腿办杂事,还带过一画室的学生杨飞云、朝戈等几位到内蒙古写生,一个月左右。当时没有任何改革的想法。第二次教师生涯,比较长,六年,期间为了英语考试不过关而落选的博士生给校方写过无数次申诉信,完全无效,完全失败。我觉得,在中国,艺术教育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谈的。在目前中国的所谓教育实践中,我最想实践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就是赶紧逃走谢天谢地,我逃走了,自由了。
杨福东:
要有一个很好的美学意识

2010年9月,我回到中国美院新成立的跨媒体艺术学院,负责一个实验影像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有两种研究对象,一种是静止图像,像摄影、油画,另一种是活动影像,也就是像大家认为的实验短片、实验影片,或者是动画、三维手绘。我希望能在教学上保持自由和开放的状态。学生到了工作室,他会有个人喜欢的方向,个人发展的趋势,工作室能给他提供一个选择的可能性,让他知道到底怎么去做。这反而对学生的要求高了,他们首要得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会有很多看不见的方向;要有动手能力,一定要亲力亲为地去做,并且假如做艺术是你一辈子喜欢的事情,那你得学会这个马拉松怎么跑,在你无聊或累的时候学会坚持。
其实学校教育提供的是一个土壤,学生虽然在跨媒体艺术学院,但是你觉得该去画国画就是画国画,该做雕塑就去做雕塑,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吸收各种养分。吸收养分不是要你变成那个养分,而是要把这些养分转换成促使你生长的东西。所以不能是纯粹的拿来主义,你得有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从学院出去的人至少有一个很好的美学意识,或者说是有很好的品质,热爱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用去苛求成为大家眼中的艺术家,前面有很多路,学生想走艺术家这条路他自然就走过去了。有时候艺术这东西是教不来的。
隋建国:
我采取相对保守的原则

我在1997当担任雕塑系主任之后,着手调整系里的教学结构,但都是逐步调节。直到2001年进入望京新校园,系里才全面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修订后的中央美院的雕塑系本科教学目标,主要是完成雕塑专业的基础教育。这其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专业基础阶段,先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对雕塑语言进行全面的介入,把从古典雕塑到现代雕塑的基本经典语言接触一遍。在新大纲修订之前,学生只被要求学习古典与写实传统这一段,这是原来中国各地的美术学院普遍的教学特点。但是新的大纲要求全面介入,因为它们都已经是人类文明的基本遗产。
第二个阶段在三年级以后。学生会自主选择进入不同的导师工作室。现在系里的工作室分几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个导师工作室:一、二工作室基本坚持古典与写实,一工作室是法式风格,二工作室是苏式风格;还有一个方向是倾向于现代部分,三工作室偏重现代材料雕塑,四工作室主侧重实验与观念;再就是公共艺术方向,因为社会需求量大,而且要跟景观结合。2010年又补加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写实雕塑的导师工作室第六工作室。第二阶段其实也是基础,是与不同语言系统相关的创作基础。这一系列调整是得到了院学术委员会基本肯定的。
进入研究生的课程,则要求学生对于专业问题进行探索,基础的技术、技巧应用为辅,更复杂的方法和法则进入课程。学生要被训练成为艺术家或者未来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因此要求学生在毕业论文和具体创实践作上对具体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但目前这里所谓的深入研究还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带研究生的导师同时也就是带本科生的导师,相对于本科生的“宽”,在研究生教学中这个“收”的动作还不够精彩,与本科教学的差异拉开的不够大。从本科到研究生这个“漏斗”形,从“宽”到“深”的过程展开的不够。这其实还是与中国整个大学教育层次的不够明确有关,不只是艺术教育的问题。
说起这些年支撑我做教学改革和调整的艺术教育理想,其实我在这方面一直有困惑,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总是比较怀疑各种时髦的国际国内潮流,也怀疑坚定不移的保守者,这些激进和坚守的姿态都会夹杂着利益的博弈在其中。当然我尤其是先会怀疑自己。在这种心态背景之下,我采取的方法无非是多出去看,欧美和亚洲都看看,为我们的教学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选择方向。在担任十多年系主任的过程中,我其实采取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原则。我所期望的似乎是一个期待和储备的状态。因为国际文化艺术舞台不断地变化,很难让一个学校跟着风头去走,况且在中国引领世界潮流之前,到达中国的信息总有相当的滞后性。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还处在相对封闭的时候,能给学生多一些选择,也给未来的发展多预留一些可能性。这有点像人才储备,让包括写实雕塑在内的这些不同的线索都能够持续下去,也许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的各类人才就会迸发出来。到现在通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其实各方面,各个方向都开始出人才。雕塑系的教师队伍积累到目前,也已经可以说是整个亚洲各国综合下来力量最强的一支。我觉得我这个相对保守的办法也还算有成效。
邱志杰:
我不相信个体的东西

我直到2003年答应回母校(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教书,也教新媒体艺术的课程。2010年这两个系与展览文化中心又组成了跨媒体艺术学院,专门关注当代艺术。目前的跨媒体学院有五个工作室,在构架上,我们的五个工作室是负责创作方面,另外还有八个实验室,帮助学生解决技术问题。我们的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观念和思想类型的,诸如下乡、社会考察、文化研究,包括讨论美术馆艺术、非美术馆艺术,讨论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等等;另一类是材料意义上的媒体,摄影、录像、剧场装置,甚至绘画类的课程。
因为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所以下乡、做社会调查在我这里的比重非常大。要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需要一定的人数基数,于是一方面在时间上跟学生别的专业学习有冲突,另一方面社会调查非常强调群体合作,因为是集体项目,这也跟当代艺术很多执行观念冲突比较大,比如,我不相信个体的东西。现在的当代艺术家表面上自以为自营,其实里面包含很多迷信: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可是你背后有画廊在控制,有策展人在暗示,其实并不自由。反而是在学院里我们有自由去从根本上想一些大问题,所以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去思考博伊斯、杜尚那样做艺术对不对,而不是受到社会上流行的成功学的控制,但是这样的思考,非常难以进行,因为社会上的诱惑非常多。
黄小鹏:
珠三角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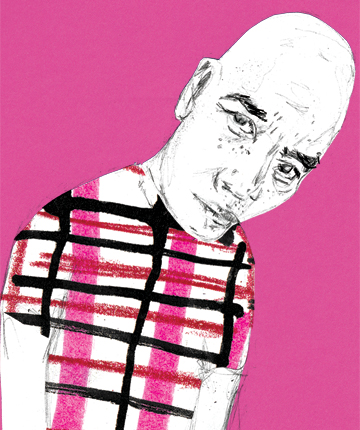
2003年,我回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并在系主任王维加的支持下,于2005年成立了第五工作室。在课程设置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模特课,当然,课程也只能根据油画系本身的框架来修改:把素描改成草图文案,色彩改为材料试验,创作课保留。在传统的教学中,素描、色彩和创作的课程是分开的,我们尽量让这些课程之间保持连续性,例如,草图文案课之后,希望学生可以在材料试验课程中延续上个课程的东西,然后在创作课程中最后呈现作品。几年下来,课程还是在不断地做各种尝试、变动。另外,每年我们都会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过来做讲座或工作坊,其中,国外的艺术家居多,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视野,对学生很有启发性。
广州美术学院所在的城市位于“珠三角”的核心区域,“珠三角”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工业和商业实验基地,其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巨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它简单粗糙的理解范畴。这种巨变为创造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为大学提供了更宽广的挑战平台和实验空间。我们的课程强调实验性,也强调逻辑思维训练的必要性。对洞察力和视觉语言的训练既来自于学生的自我的内在潜力,也得益于师生一起的探讨,我们相信,新的艺术语言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其中涉及上下文的关系,在当代的语境下对中外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理解和继承。
张培力:
以创作来带动教学

我现在是跨媒体学院具体媒介工作室主持人,负责本科的高年级学生创作和研究生教学。在新学院成立前,我原来的新媒体系学生在毕业后,有的还会做跟这个专业稍微沾边的事情,有的就去了银行,还有的去当公务员。我觉得这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因为很多学生是被迫来上美院的,文化课不好,又要读个好学校,以为这个系可以学软件,其实我们学软件的比重非常小。你跟他谈当代艺术,很多人没法进入,老师和学生都很痛苦。而那些想学并且有能力的人却被现行的教育制度排斥在外面了。
我们尝试在教学里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提出的口号就是以创作来带动教学。这有我自己的经验,也有对西方、亚洲其他国家学校考察后的借鉴,我们所有的课程里都是要求学生考虑作品,而不是作业,作业是个很简单的练习,可以没有思想,就是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而作品的要求则不同,作品是要表达的,我们反复提醒学生你要很清楚你想说什么,有了这个问题才有第二个问题,该怎么说。我们不像传统艺术,不要求通过磨练技能来提高艺术表达能力,而是希望两者齐头并进,一方面了解技术,一方面是对语言的认识和态度。所以,我们有些课程会把技术的门槛放得尽可能低,点到为止。我一直怀疑只有掌握了技能才可以发展自己的语言这样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技能可能会屏蔽想象力和创造性,屏蔽个人特征,因为每个人的特征不一样,需要的技能也不一样。
我们开的课程也有技术含量相对高的,比如网络、编程、互动,也有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技术的课程,比如肢体语言,这是文慧开的,还有实验剧场、机械装置等等。我们会把技术门槛降低,但有些是必要的,比如声音、数码摄影、录像、网络、编程基础,这个是必修课,二年级进入系里必须要过。之后是年级之间打通,选修课程,两个年级合在一起,比如现在两届60个人,按照15个人一个课程,每个阶段有四个课程,完全不重复,平行进行,学生可以选自己课程。这样他们慢慢会意识到自己要做选择,知道自己的趣味,哪些是对自己有意义的。
“选修”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尝试。我们的课程有一大批是一线的艺术家来做“workshop”,学生以前在杂志、网络上看到过他们作品,但是真的面对面接触、交流影响会非常大,既然学生将来迟早是要面向社会,那么很多概念与标准就不能过于封闭和学院化。让他们清楚学院之外的创作,会与学院的教学形成互补,这些课对毕业后还在创作的学生影响特别大。我们也有大量的理论课程,比如国学,这是我们自己安排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西方电影赏析、录像史、摄影史,这些理论课也会开给他们一些书目。我们的课外讲座是学校里频率最高的,每个月有很多次,路过杭州的批评家、策展人、大学教授,我能请就请,学生参加的热情也很高。
潘公凯:
当家人是要算账的

我2001年刚来中央美院当校长的时候,学校只有7个系9个专业,600多个学生;现在是7个分院30几个专业,5000多个学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央美”就是以造型美术为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九十年代末增设了一点设计专业。而这十年以来,欧美主流美术学院所有重要的专业我们都有。九十年代,我们跟西方可能是“1跟10”、“2跟10”的差距,现在是“9和10”的差距。
“央美”现在拥有最完整的学科设计。比如我们最早设立了建筑学院。在欧美,一两百年前美术和建筑完全是一码事,民国期间的美术学院,建筑和美术也在一块,“央美”只是回归了这个传统。“央美”还是美术学院里最早设立汽车设计系的,为了请来汽车设计的教授,我到日本给对方上课做交换。现在中国成了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设计师。还有一些新的专业包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艺术管理学系,一办起来就是最好水平。
现在“央美”输出的60%都是设计师,这是十年间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原来人们叫小美术,五六十年代对于“美术”的概念就是画画。二战后西方整个改变了,从纯艺术转向大美术,他们的美术学院都有设计专业。在纽约,美术学院80%的毕业生都在做设计,20%甚至10%在做造型艺术。在商品极大丰富的市场经济中,设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不是一个趋势,而是一个事实。
“央美”肯定是培养精英的,但精英教育非常复杂,不是说把学校办小了,就一定能培养精英。师徒传授的办法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推行,学校没法弄。上大课不一定就培养不出大师,我们希望出大师,但没法制定一个专门培养大师的课程或菜单。学校面对的是中段学生,它不能按最笨的学生来设置,也不能按最聪明的学生来设置。学生尽量挑得好一点,但也不是说把英语考试取消了,就一定能挑到好学生。所有考试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艺术领域尤其没有标准,硬考的目的是表明教育的公正性。
教育改革是跟整个大环境联系在一起,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校长就得去克服困难,改革要得承担责任,大家全看着你,我成了一个发动机,得自己制定方案,不能商量太多,也不能把困难都告诉大家。大家提意见说学生招太多了,以前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多好,所有的学生认识所有的老师,气氛多温暖。但社会要往前走,不要老是怀旧。要学科跟国际接轨,就得扩大招生,就得盖房子,一环接一环,没办法的。有人说,高校缺的不是大楼,是大师,但如果没有大楼,都是茅草屋,大师也都跑光了。当家的人是要算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