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伤痛记忆—从台湾的角度
| 2012年04月17日

传说中的谢德庆,本来只能从残篇断文中才能拼凑出蛛丝马迹。自从谢德庆1985年宣告以不做艺术为他的行为表演以后(《一年行为表演1985-1986》,纽约),台湾有关他的讯息愈来愈少,这次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演讲、又是座谈等一连串行程,在台湾艺术界确实激起一股对他好奇超过对他有兴趣的热流,尤其在他的粉丝中年轻人占着重要的一群,更令人瞩目。而时间落差所造成的解读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谢德庆表演的身体历史脉络被移置掉,以至于今天对于谢德庆的阅读完全脱离了在地论述,而直接接引了美国的全球化论述,本文就将从这一段历史的遗忘作为开始。
正是在谢德庆“不做艺术”(《一年行为表演1985-1986》,纽约)的迄年(1987年),在三十九年的戒严状态之后,台湾面对了解严的来临。今日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像,当谢德庆在台湾发表他的第一个作品的时候,台湾正处于高压统治下冷战/反共/戒严的年代。1973年谢德庆在台湾发表他的第一个作品《跳》,他从大约有十五英尺高的二楼跳到水泥地,使他的双脚脚踝遭到伤害至今仍存在着后遗症。这个身体的记号是他首次为自己立下一个孤高的“叛逆者”的身体坐标,乃至于1974年他断然迁徙自己的“跳”船事件,都可以说是这个身体伤记在自我意识化的过程中,渐渐翻转出他的身体现代性的欲望,行动力学在这里找到支撑世界的着力点。因此,1973至1974年也是在一个冷战/反共/戒严的年代,我们现在回头看谢德庆从“跳楼”到“跳船”的行动,就更能彰显在压抑的历史情境之下,他的行动在其中所意味的非法性,从肉体损坏到国籍破坏,都是他在跟台湾的关系转变中对世界的告白。
1978年谢德庆通过他的两个作品《蜡笔》和《半吨》继续进行他的肉体损坏,前者让自己的左右脸颊用美工刀划出两道血痕,后者则让自己受半吨的石灰板重量,而导致锁骨断裂。在他偷渡到美国之后,也是1978年在他开始《一年行为表演》系列作品的首作“笼子”(《一年行为表演1978-1979》,纽约)之前,他的世界观尚处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状态,或者也可以说是处于现实与非现实的断裂线上,据他自己说是跟“当时的确处于一个底层的不利地位”(《现在之外》第330页)有关,所以他在《蜡笔》与《半吨》其中布满的死亡性,其实是从生活与劳动的孤立状态中,牵引出来的一种自闭的变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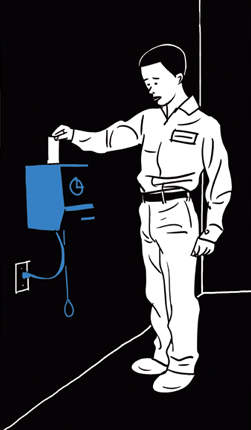
谢德庆曾于1973年在台湾发表过一个画作《军人身份》:“在画布上分割出两块长方形,在下半部涂上军队的草绿色,在上半部白色的中间写上我的兵籍号码”(《现在之外》第325页)这是他曾被征召服兵役的记忆。若从跟他本人的谈话与他的采访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本人对于曾经处于戒严时代的台湾并不多谈,甚或轻描淡写,例如他说:“我在1973年停止绘画。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当时台湾的整体环境十分压抑,几乎没什么机会可以掌握到激动人心的西方世界前卫艺术”(《现在之外》第328页)。然而他并没有进一步谈到那个让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戒严年代,到底禁锢了他的“身体行动➔肉体欲望”的记忆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即使当时在他《军人身份》这个画作中,已将某种自己经验过的真实世界做了结合自我意识的表现,也就是社会关系随着人们经验过的现实社会而生产出自己的身份,但是最终谢德庆表现了在军事戒严下的“军人身份”,只有他的兵籍号码的数字,却没有他的姓名。
我们仍然记得在那个冷战/反共/戒严的年代,身体被风声鹤唳下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氛围所禁锢,文艺青年所有的自我学习都来自各自的孤立状态,一种在自闭的耽溺中发展出来的特定的知识形态,如同谢德庆自己说的,他的思想影响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尼采、西西弗斯等人,可以说这几乎就是欧美现代主义的脉络了,然而相对于谢德庆当时受到压抑的环境而言,这个脉络勿宁成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神话。1987年解严之后,政治界与学界重写戒严时期的历史,出现了甚多以后涉及历史的方法论论断的二元化史观,包括对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历史发展的批判理论,往往以“自由”之希求为批判的基础,提出对于戒严时期的美学价值、艺术规范及审美经验的修正,这种批评流于以今非古,因为正是这样的批评造成了脉络的零碎化,覆盖了真实经验中身体在迷雾中流离的伤痛记忆。
无怪乎这次台北市美术馆邀请谢德庆来台参加《现在之外》一书的发表座谈会的时候,主办者的着眼点还是在西方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中,建构从台湾出发到美国/纽约实现艺术梦想的谢德庆,如同《现在之外》作者希斯菲尔德在这本书所言及有关谢德庆的行为论述,都是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的脉络下,所伸展出来的一套层次完整的言说。这一点也让我们了解谢德庆为何公开承认在台湾的第一个行为表演《跳》,并不是一个好作品,虽然希斯菲尔德评价为“迷人的作品”,双方的落差点还是要回到谢德庆本人想要在美国重新开始一个跟台湾脉络毫无关联的自我论述脉络,这就是他在纽约《一年行为表演》的开始。

然而当我们面对一位亚洲/东北亚/台湾出身的当代艺术家如谢德庆者,要如何从在地的历史出发,对谢德庆行动身体的现代性欲望作出诠释,这是一个亚洲/东北亚/台湾的艺术评论家不能逃避的问题。譬如:当我们面对谢德庆的问题,我们是否要顺着谢德庆的自我论述脉络,将《一年行为表演》,与其在台湾做的早期行动完全切割开来,就变成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建构谢德庆作品论的脉络所不能逾越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重新审视台湾当代艺术论述如何被建构问题的路径,然而在这次谢德庆在台湾被众多学者讨论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完全的被忽略了。
我们还是要追问:亚洲/东北亚/台湾出身的当代艺术家如谢德庆者,他们对行动身体的现代性欲望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艺术评论家陈传兴在1992年出版的《忧郁文件》一书(雄狮图书)序文中提到:“虽然原本在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先天上即已是不对称和割裂交混的离离合合,但却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延迟割裂现象,这是否是台湾特有的文化区域现象?”当谢德庆声称《一年行为表演》的作品思考角度,都来自相同的前提“生命是一场终身徒刑”时,似乎替陈传兴的问题暂时找到一个答案。
台湾人当代的身体图像,从现代史来看,跟身体禁锢有很大的关系,假若日本殖民政府把他们的现代化经验移植到台湾来,那“北刑务所”(国民党来台改称为“台北监狱”)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早在十九世纪末,西方世界采用的中心幅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空间即已出现在台北,其巧妙的、经过精算的空间构造与权力关系,成为台湾早期现代建构的原型,这说明了台湾人的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尚未生产个体性之前,竟然是先从监禁开始生产身体意识的。我们若根据福柯的研究倒可以知道,这是巧妙的、经过精算的关于身体如何被一种规驯的现代科技观所掌控,可以说身体的规驯是建构社会之现代化的重要过程。谢德庆于1978年发表他的两个作品《蜡笔》与《半吨》,仍继续进行他从《跳》以来的见血仪式,仿佛他在进行一项肉体重建工程,想要借由自我毁伤的方式从台湾历史这个监禁的身体脉络中逸脱而出(奴隶是无权伤害自己身体的)。他的表演从而是一场身份认同的洗涤仪式,而此后台北文艺圈与美术学院对他的大力攻诘,更可反证这种其内即其外的高压掌控。1978年他开始《一年行为表演》系列作品发表,充满影像的竟是以纽约作为整体记忆的背景。

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长达三十九年的戒严,以禁锢国民自由思考与身体活动的方法来强化国家纪律,那时“台北监狱”实承担着公开/国家暴力的展示功能。谢德庆在这样“保守而乏味”的环境里所浸淫的身体性,弥散的不只是当时戒严政治的气味,更包含了禁锢的历史脉络所制造出来身体与现代性的关系,简单说就是对自由之希求,严格地说乃是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言。与其说谢德庆是在向往自由的国度之下成为非法移民,勿宁说他是在“几乎没什么机会可以掌握到激动人心的西方世界前卫艺术”的封闭环境之下,向往美国作为他的当代艺术应许之地而已。因此他的从“跳楼”到“跳船”的行动,也是从肉体损坏到国籍破坏,都在表现这个简单的对自由之希求。当时在那个冷战/反共/戒严的年代,美国因第七舰队防守台湾,而在岛内大力塑造它安全的守护神之形象,谢德庆在几乎是对西方世界前卫艺术的封闭知识之下,决定选择了美国作为他的应许之地,此一决定的前因后果,不知是否即为陈传兴所谓“台湾特有的文化区域现象”是也?
谢德庆说把生命当做是一场终身徒刑,当然意味是他对自己生命史的一种观点,这话说得有东方玄学之妙,但也有一些历尽沧桑之叹,既可以用来诠释自己的创作观,亦能够显示出他把身体跟意义结合起来。然而就意义而言,身体在意识形态的生产体制中,个体性是从自觉自己的存在意识开始,通过伤痛的身体感觉(如笛卡儿所言)而震荡出与身体紧密结合起来的自我存在意识,个体性于焉完成。这种通过努力而表现出来的主体,说是“徒刑”之苦亦不为过。所以谢德庆不管是1978年之前在台北、纽约的作品,或是1978年之后创作《一年行为表演》系列作品,他所受的“徒刑”都是来自伴随着身体苦痛的感情而做出的努力感,说得更具体应该是他就是为了要成就他的应许之地。
当谢德庆从亚洲/东北亚/台湾出发,到了他认为的当代艺术应许之地,虽然他说:“在概念上,我的作品并不必然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与场址产生关联”,然而他也说他建构的作品脉络就是在纽约这座美国城市执行,潜台词是否也可以说他要他的艺术与冷战/反共/戒严的脉络切割开来。切割掉他从肉体损坏到国籍破坏的记忆,切割掉由台湾转向世界的原因与过程,他的伤痛记忆,如今竟然成为他的忘却史,也许西方当代艺术所需要的,更是一个“全球化”的传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