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银座时代的游戏:东京当代艺术
| 2012年05月21日

日本艺术刚刚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高潮。草间弥生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赢得了评论界的盛赞;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为物派大师李禹焕举办个人回顾展,令其成为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艺术家;此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将在今年年底开展一个关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之间的东京实验艺术的展览活动。然而,如果说几十年前日本战后的文化输出如今在国外收获了迟来的成功,那么现在进行时态下的当代艺术在日本国内的情形则似乎有点儿滞后了。正当日本的硬产业为打破“加拉帕戈斯综合征”式的孤立主义心态,拓展外国观众和客户群而共同努力之时,本土的画廊则尝试着在国外未经检验的新兴市场定期推介他们的代理艺术家。
像香港这样的亚洲艺术中心配得上真正的国际大都市的称号,而东京往往总是显示出强烈的地方保守性。继高古轩和白立方在香港设立其“前哨站”之后,法国Perrotin画廊和纽约Lehmann Maupin画廊也通过香港艺博会首度试水,随即紧锣密鼓地计划从此城市开始挺入亚洲市场。从画廊国际背景的多样化来看,东京落差太大,根本无从与香港相提并论。
人们对此常常归结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日本的当代艺术藏家并不多。在画廊的传统的聚集地—东京的银座,日本传统艺术和工艺品仍然受到明显的偏爱。那里的画廊绝大多数还在沿用古老的艺术“租赁”制度,即画廊让艺术家每周付30万日元来展销其作品,其中不含任何展览策划,而东京画廊是他们中的一个重要的“异数”。东京画廊由山本孝1950年创立,是当时日本首家当代艺术画廊。它曾支持过日本好几拨先锋艺术家的创作,例如具体艺术协会,以及成形期的物派艺术团体,在过去十年中,东京画廊似乎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倾力打造亚洲内部的链接,尤其是与中韩两国。
东京艺博会也在发生类似的转变。作为今年的新任总监,金岛隆弘被视为领军冲刺国际舞台的理想人选,倘若真有这一人选的话。金岛隆弘曾担任东京画廊在北京的实验项目“北京东京艺术工程(BTAP)”的总监,现在亦同时监管“远东当代”这个位于横滨的偏向于展示中国艺术家的策展机构。尽管金岛隆弘试图让东京艺博会取得更为亚洲化的定位的意图很清晰—参看今年的新单元“探索亚洲”—但是,事实表明,这个艺博会已经很难被视为东京最优秀的当代艺术的展示平台了,因为它对古董、瓷器和工艺品的经销商也同样表示欢迎。无论如何,除了包括阿拉里奥画廊和耿画廊在内的东亚忠实拥护者组成的精英小集团以外,很少有国外画廊会选择把东京列入其全球博览会参展日程表之内。倘若香港国际艺术展似乎已将其定位为以西方艺术为主打的亚洲顶级艺博会,那么东京艺博会的最佳押注方式就是把重心转向模糊意义上的北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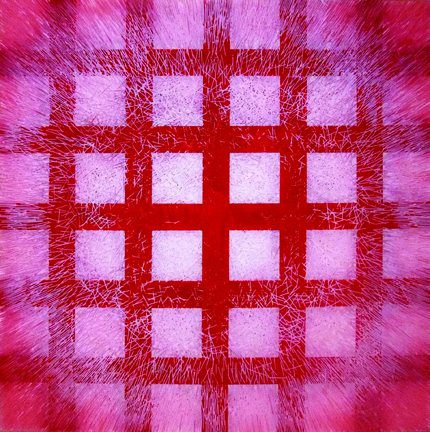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东京最为国际化的几家画廊已决定跳过东京艺博会另辟财路了。Taka Ishii画廊、Shugoarts以及SCAI the Bathhouse全都是欧洲的巴塞尔艺博会和Frieze艺博会的常客,也是亚洲前途大好的香港国际艺术展与艺术北京的固定展商,他们都曾通过这些艺博会为其代理的艺术家成功觅得国际关注。Shugoarts画廊的佐谷周吾说,“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亚洲市场本身,去年我们首次退出东京艺博会,参加了G-tokyo艺博会(2月份的一个仅有15家画廊参展的规模较小的‘精品’艺博会)。我们确定,参加东京艺博会对宣传我们的艺术家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说不参加东京艺博会的行为相当于背叛了脆弱的国内当代艺术市场,好几家日本顶级画廊已开始积极寻觅新的藏家据点,尤其是加强与亚洲藏家的联系。就在不久前,东京的田友美惠画廊的艺术家还几乎清一色的是日本人,但在今年1月的“艺术登陆新加坡”博览会上这个画廊宣告其代理的菲律宾“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家罗德尔·塔帕雅的参展作品已全数售出。今年稍晚时候,大田画廊、三潴画廊和小山登美夫画廊在新加坡吉门艺术村设立的分馆即将揭幕,由于这些画廊所经营的工艺性强并带有新日本画风格的艺术正好与印尼、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藏家的趣味相投,那么他们纷纷在东南亚建立据点也就合乎情理了。
当东京老牌画廊带领着那些已然声名赫赫的艺术家驰骋国际的时候,一帮年轻的艺术经纪人则一直在为那些不能被置于仍然贴在日本当代艺术上的“超扁平”或“微波普”等概念标签下的艺术家得到国内外的承认而默默努力着。正是这拨在老一辈丰富的艺术经营经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艺术经纪人才是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推动者。
该协会所推介的年轻一代艺术家敢于猛烈抨击关于日本艺术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自打村上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风靡海外的“超扁平”理论之后,这些观念就几乎不曾动摇过。Take Ninagawa画廊是“新东京当代艺术”画廊协会的成员之一,画廊的总监是曾在纽约做策展人的蜷川敦子,以及艺术家竹崎和征。去年整个日本只有该画廊参加了新艺术经销商联盟(NADA)艺博会与Frieze艺博会,此外,该画廊与日本特色亚文化—例如heta-uma(故作笨拙或技巧“差劲”的好艺术)—过从密切。Arataniurano画廊总监为荒谷智子和浦野睦,他们早年都曾为著名的SCAI the Bathhouse画廊工作,以做户外装置著称的明星艺术家西野达是该画廊的压阵艺术家。“无人岛制作公司”由三潴画廊前员工藤城里香创建于2006年,画廊所代理的“边缘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与美学趣味都与东京的主流当代艺术保持着距离,他们运用非传统的媒介,作品形态跨越表演、漫画、音乐与声音艺术之间的界限,这种富于变化与流动的创作方式令人回想起多年前东京艺术界的状态。生于俄罗斯的策展人罗迪恩·特罗菲姆琴科掌管的Frantic画廊声称其使命为“抵制日本当代艺术的呆板僵化的形象和模式”,这种胆大无畏的口气也令人忆起往昔东京的真正的前卫风范。Frantic画廊偏向于代理村山诚和田附楠人这类艺术家,其作品忠实地反映了日本艺术学院长于传授的精雕细琢的美学特点,与此同时回避了那些国内外喜闻乐见的轻巧易画的波普图像。

但或许是“国际化”话语本身存在问题,并不只是因为东京的画廊需要将国际化当作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借此克服狭小的国内市场的局限,也不是因为要顺理成章地延续国内的成功才在近来入侵亚洲区域。如同特罗菲姆琴科所指出的,国外艺博会已成为超国家结点所组成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它完全摆脱了“国内-国外”式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样是向日本美术馆的策展人介绍自己代理的艺术家,在国外的艺博会现场就绝对比在日本国内的展览上更容易。”这种“反向进口”策略—先在国外积累艺术家的名声,然后再寻求本土语境中的合法性—似乎在其他亚洲国家也同样很流行,这些国家通常是在文化产业长期受制于西方的情形下努力博取自身的地位。而这种焦虑感或许正是东京艺术界所需要的鞭策力量。
就在规模空前的村上隆个展“自我”在多哈开幕的前夜,这位足迹遍布全球的艺术家与日本两家文化艺术杂志的编辑进行了一次论辩,村上隆向日本整个这一代年轻艺术家发出谴责的声音,认为他们缺乏沟通技巧,对国际当代艺术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或许村上隆有他的道理,或许这些艺术家的确需要像东京年轻一代画廊那样给自己配备国际化大都市的头脑以及社交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