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与译介——理论引进的两种模式
| 2012年05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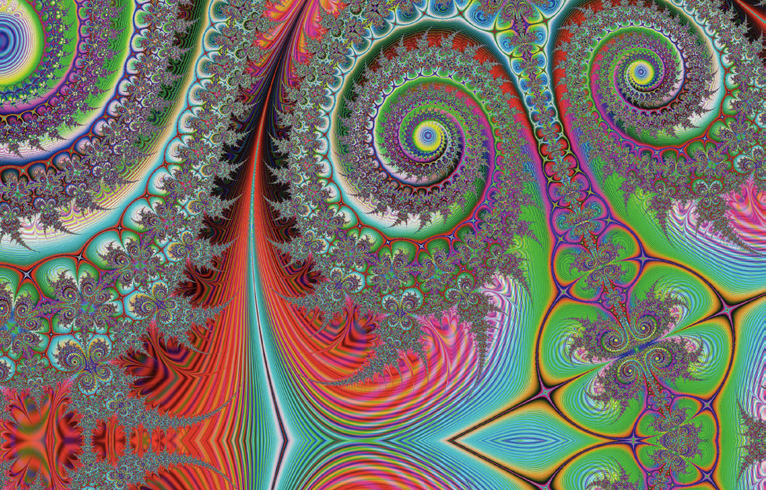
对于只有30年历史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也有过一波又一波的西方理论潮流。从1980年代起,“存在主义”的流行—也在作品中留下了直接的印记,比如钟鸣的《他是他自己—萨特》;“后现代”理论进入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一度在批评文章中被大量直接引用;而最近的一波潮流里包括阿甘本、巴丢、朗西埃和齐泽克,以及鲍里斯·格罗伊斯、汉斯·贝尔廷等。作为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走红的理论家,中国学院内对他们并不陌生,只不过专门研究和从事翻译引进的学者并不多;而在民间,通过豆瓣小组这样的在线平台,或是像“泼先生”这样的网络杂志,再或者像王立秋这样活跃的译者,加上一些更加“小众”和零散的翻译,以及类似乔纳森的这种专司给翻译“挑错”的博客存在,组成了现在民间翻译的活跃。而在艺术圈的一些译者的译介可能更有选择性和针对性。但此类翻译虽然快速即时,目前却鲜有经过严格编辑的正式出版物。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作为在中国非常红的一个理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在2012上海双年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受到的热烈待遇跟另一位联合策展人扬斯·霍夫曼大相径庭。虽然国内对格罗伊斯的翻译也并不系统,但通过艺术圈内一些译者的介绍—他的一篇《弱普遍主义》曾被广为流传,格罗伊斯的知名度在中国艺术圈内显然大大超过霍夫曼。当然也有人批评在翻译引进时对理论本身缺乏批判的态度,声音总是倒向一边;译本质量参差不齐,并且在选择某个理论家的著作时无一定规律可寻,其最重要和最具相关性的著作未被翻译。至于为什么现在这些统称为“法国激进哲学”或者“新左”的理论/理论家在艺术界的走红,有种解释是,艺术家通常偏左,尤其现代艺术以来,艺术家都在充当“先锋派”的角色,对文化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否定的激情在—艺术要更新人们麻痹的感觉,无论是感觉还是观念,都需要走前沿,如同一种天职。艺术家更易和激进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不过也有人在提醒,这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些理论和中国的语境之间的衔接。我们采访了汪民安和沈语冰两位在“译介”上同时又和艺术圈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学者,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潮流的影响力
汪民安
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
—“1980年代是全民读哲学,不仅是艺术家,包括搞理论的、工科的都看哲学书。1980年代读是社会风潮;今天读的是真正感兴趣。我觉得现在读得最多的是艺术家。”
汪民安说在他1988年进入大学之前,国内对西方哲学和理论的引进就已经很活跃,那时流行的是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他进入大学后,这些人慢慢过时了,开始了“后现代”,当时读的是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只是不同于1980年代翻译界的热闹和混乱,后现代理论在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并不多。
1995年汪民安硕士毕业,开始翻译一些小文章,包括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一些论文。读博士时他和几个同学翻译和编辑过一本《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我确实可能真正是理论界最早跟艺术界有关系的。一是我读的这些东西,像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都有很多谈艺术的文章,我很早就读过德里达讲凡·高的《艺术中的真理》,那本书到现在还没翻成中文。后来读书越来越多,知道国外的哲学家没有不谈艺术的,而且他们不仅懂当代艺术,包括电影、音乐、建筑全部都懂。我在这方面也有兴趣。”他来到北京后认识了黄笃,偶然接触到艺术圈,并且在《今日先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展览评论。当时北京的艺术家圈子很小,很快就结识了一批人。随后汪民安也以对德里达、罗兰·巴特和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理论家的翻译为人熟知。

而国内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追随着国际学界的潮流,艺术家们谈论的东西也与此相关。汪民安说他主编的《生产》杂志在2005年时制作了一期阿甘本专辑,那时国内还没有人谈过阿甘本,2006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阿甘本的文章;2006年,他向国内引进翻译了巴丢,那时巴丢在国外刚刚流行。不过国内和国际潮流还是存在一个明显的时差—“阿甘本在美国流行应该是比在中国要早十年,他那本书《牲人》(Homo Sacer)可能是1996、9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2000年以前他在美国就非常流行了,我们首次介绍那本书是2004年,我翻译了他几篇文章,中间有个五六年的差距。”
汪民安说,这一批理论家的走红,很多是因为他们是上一代哲学家的重要阐释者,比如阿甘本之于福柯,巴丢、齐泽克之于拉康等,同整个1960年代法国的理论都有关联。“学术界也是赶风气,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他们从1960、1970年代开始红,一直红了30多年。30多年之后被完全消化了,美国学术界把他们消化得非常熟了,已经没有新鲜感了。美国的学术界总是要找新星,跟艺术圈是一样的。现在流行的哲学家阿甘本、巴丢、齐泽克恰是他们的学生辈。如果从原创性、重要性和历史地位来看的话,他们这帮人和上面是没法比的。美国贡献不了大师,但是这些大师必须到美国去走一遭。美国承认你之后,全世界就会承认你,他们的评价体系很强,确实能发现真的好东西。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判断力,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介绍阿甘本,根本不是看了阿甘本什么著作后就介绍了,而是他在美国已经很厉害了,我们才把他介绍来。整个学界,前十年像福柯、德里达流行,再过几年德勒兹流行,然后再过几年阿甘本、巴丢、朗西埃流行,这很大程度是跟着学院潮流在走。”
不过目前国内这类书好的译本并不多,网上流传着一些单个的文章,但相对于这些理论家的整个著作而言实际数量非常少。即使目前最流行的几位理论家,每个人正式翻译出版的译本也不过一两本。“实际上翻译过来的书非常少,但已经开始买版权了,比如阿甘本的书,我给北大出版社联系的,大概买了四五本。”
“说实话,我不觉得艺术家非要去读理论,真正好的艺术家或者大的艺术家自身就是哲学家,根本不需要去学哲学。坦率地说,我觉得国内没有几个艺术家真正懂这些问题。可能相对了解的深一点是汪建伟,他是我接触到的艺术家里唯一的一个真正能谈理论来龙去脉的。他谈齐泽克基本上跟我们学术界同步。”汪民安说。但这两年他碰到的艺术家都喜欢和他谈哲学,尤其是做影像和装置的。前五年,没有艺术家谈哲学,这几年普遍地突然喜欢哲学,先是福柯、德勒兹,现在是阿甘本、朗西埃。“他们好像都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兴趣特别浓。”

艺术史的学科建设
沈语冰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代美学、现代艺术史与观念史,著有《20世纪艺术批评》;译作包括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等;主编“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等。
—“作为研究艺术史的人,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基础比较浅薄,尤其是文献欠缺。”
作为一个“不在现场”的理论工作者,沈语冰做的大量工作是艺术史的学科建设,他的研究由现代主义开始,延伸至当代。在沈语冰看来,我国对西方现代主义近100年历史的消化和吸收是苍促和粗糙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的近100年时间内,西方除了有强大的艺术运动,还有100年的艺术批评史,100年的艺术理论史和美学史。在国内,现代主义这一环是缺失的,为国内的艺术研究补上这一课,是沈语冰目前的工作重点。“补课”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意味着对一些重要的西方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们正在分工协作地进行。这一点也使得他被一些人称为“书斋型学者”,沈语冰并未亲自参与到中国当代艺术“如火如荼”的发展中。但在已出版的译作中,从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到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再到列奥·施坦伯格的《另类准则》,正如他在《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2010年)导言中所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翻译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西方的学术思想简单化。如果没有详尽的文本翻译,有的只是几篇通论式的介绍,那就很难避免简单化”。同样在此书中,他将西方美术史、美术理论和批评分成了四个板块加以介绍,这反映出了他的基本思路—“图像学、艺术的社会史”,“精神分析、风格理论与视知觉理论”,“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后现代主义”,其中涉及到的不仅有沃尔夫林、罗杰·弗莱、潘诺夫斯基、夏皮罗、贡布里希、T·J·克拉克等重要艺术史家,还包括格林伯格、施坦伯格、迈克尔·弗雷德、罗莎琳·克劳斯、哈尔·福斯特、伊夫-阿兰·博瓦、本雅明·布赫洛等当代最杰出的艺术批评家。
沈语冰坚持现代性的社会分工原理:美术史的研究是学术,而艺术创作就是创作,两者有所区分,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意义只体现在学术史中,没有义务去指导实践。“从古希腊人的区分来看:研究理论的科学属于理论或哲学,研究创作的学问属于诗学,哲学属于理论范畴,创作属于实践范畴,是两码事。”但是,他也承认实践与理论混合的工作模式是众多模式中的一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代艺术的创作越来越跟理论产生一种胶着在一起的状态,西方甚至有很多大学设立‘诗学’博士学位,培养实践型的艺术家,而不是理论型的艺术史家或美学家。以前一般认为,艺术家是不需要读博士的,最高学位就是艺术硕士,而现在西方的一些大学里,理论与当代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这可能是一种趋势,是好是坏现在还很难说,可能要等到20年以后,才能看出来。我反对的只是:这种将理论研究弄成实践本身(比如有些理论研究变成了文本写作游戏),又将实践弄得越来越理论化的做法,是唯一好的做法、可行的做法,也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做法,等等。这种无视分工的思想,是典型的后现代的想法。而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仍然是遵循现代性的社会分工原理,老老实实地做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把西方100年现代主义历史慢慢消化,不必急于求成;现代性的某些核心价值的建设是绕不过去的,一下子跳入后现代的做法,只会欲速则不达,使我们陷入前现代性的不断轮回中。”
沈语冰坚决反对现代主义艺术史已经“过时”,我们只需面对当代艺术的看法,他认为学理的脉络不能人为地切断,离开了100年现代主义遗产则无法奢谈当代艺术(例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离开了巴黎独立艺术家协会的独立沙龙展以及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章程等现代主义机制,根本就不可能诞生杜尚的《泉》)。按照西方的标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似乎有一个清晰的线性发展过程,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现代主义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在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全部混杂在一起了。“中国还有很多东西是前现代的,甚至说是封建的;有些是现代的,比如说某些私营企业的管理;还有一些,比如在前沿理论方面,则是后现代的。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沈语冰说,“彻底的‘拿来主义’中存在着巨大的危险,这使得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是当代的,就是前卫的。殊不知,有大量搞当代艺术的人,其理智水平还是前现代的。”他认为学术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艺术家或许无需大量阅读,对理论或许无需研究得很深入,但一定要达到一个时代的理智水平。而这个理智水平,固然得益于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混合探索;不过不直接介入实践的学术研究同样也在为它的形成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