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问题:第五代海外华人艺术家
| 2014年01月13日

2012年,有机玻璃、金属、吸声海绵
100×40厘米
在历史学家孔飞力的总结中,中国的“现代”移民开始于16世纪早期,至此开启了华人对外移民的四个阶段:早期殖民时代(16—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时代(约19世纪中叶至1930年);亚洲革命时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和全球化时代(20世纪以后)。对于艺术家而言,据艺术评论家费大为观察,从1887年李铁夫留学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出国留学的青年画家3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过四次艺术家移民潮:第一次是1949年前后,代表画家有赵无极、吴冠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艺术潮涌般进入国门,美术思潮空前活跃。一些艺术家对西方现代流派产生了浓厚兴趣,再一次踏出国门,如袁运生、罗中立、陈丹青、陈逸飞、周春芽等。接下来便是2000年以后,人数多不胜数,尽管目前这批人所获得的成就没有前人瞩目,但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文化背景下,却值得持续关注。
在今年9月16日于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的“在地未来—文化中国·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邀请展”,可谓是近年来国内首个针对海外华人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本次展览关注并呈现了来自13个国家,22位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这些艺术家,或是在国内接受了基础教育后留洋深造并留在当地生活,或是移民家庭的“洋二代”。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海外华人处在一个“空间共同体”和“时间共同体”之中。“空间共同体”指的是“共同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归属”(情感上和经济上),不会因为他生活于千百乃至上万英里以外而受到影响。相反,“分开生活”却可能是指一个家庭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却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这两个共同体并不是中国家庭所特有,但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移民中更是如此。策展人冯博一表示,每一个海外华人艺术家的身份都是独特的。他们作为一个既包含差异,又具有共同身份的创作群体,在多重文化碰撞、交融中从事视觉艺术创作,难以占据中心位置,因此他们长期被忽视,所以期待透过身份认同,挖掘他们的内在价值,是本次展览的意义所在。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洋二代”海外青年艺术家廖丁婷的作品被放置在展厅的入口处,异常显眼。这件名为《入侵》的装置艺术:一个个红色的小盆栽牵着一根根风筝线,但线被一个窗格拦腰截住,穿过磁铁和锋利的刀片,风筝只能挣扎着仰望飞行。作品上的风筝是她家合法公民身份文件的复印件,其中包括她的祖父母在印尼建国前,注明其是中国人后裔的证书。这些来自家庭的文件,试图唤起两种迥然不同的感受。一方面,它意味着其与遥远祖先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备受排斥的感受。廖丁婷用流利的英语介绍,由于印度尼西亚不鼓励中国文化的传播,因此他们在家中也用英语对谈,导致她至今一句汉语都不会。“有时我会很困惑,我怎样才能找到文化的根?我不认为世界可以武断地分为‘东’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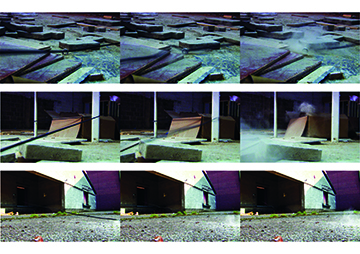
2010年,单屏投影,58秒,循环播放
在日本留学的刘茜懿是另一个典型例子。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的邻居和朋友都会跟她保持距离感:“我们中间像隔着一块玻璃一样”。出于极度的孤独,她躲在房间里长时间创作,最后迎来了她风格的转折。其作品《天籁癞》讲述的正是一个80后女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片中的八卦盘象征着天地和万物的命运,最终女孩打破了属于自己的那个罗盘。这恰恰就表现出她自身的创作轨迹:“正如这样,我的基础是在中国打下的,但我的爆发却是在日本。”令她意外的是,她的作品,日本观众的反应和中国观众差别巨大。因为她的作品涉及到“性”,日本观众会觉得中国的80后竟然如此开放,而中国观众则会认为她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从今年的众多青年展览中,都能看到作品“小清新化”的偏向,这种作品倾向主要表现为精致化、去政治化和个人化。即使在表达对政治或身份的诉求时,也是温柔的。像同样表现与日本的邻居关系,获得本次展览“新锐奖”,来自日本的华人青年艺术家潘逸舟的作品《邻人》,以仿真玩具的游戏化方式,通过影像表现了两部由炮筒连接的坦克,所形成的相互角力、牵制和消耗的过程,象征性地比喻了邻国之间既“不能分开”,也“不能共舞”的冲突与依存的关系。面对这个问题,作为评审的费大为认为:“新世纪海外华人艺术家,基本上是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太考虑文化对话的问题,他们的作品也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国籍的标签,他们更多的是表达个人观点。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叫‘留学生艺术’。这次展览可视为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而作为参展艺术家之一的高洁则认为,在他们这些“年轻的国际艺术家”身上,文化身份元素是一个过于明显的语言。这种选择是一种明确的指向,会直接消解掉解读作品的其他可能角度。并且,明确的象征符号也会明显妨碍观者进入更细腻的深层解读,让观者难以体会作品的真正核心思想。因此明显的文化身份符号经常成为对解读作品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