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 2014年09月11日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因其《关系美学》一书,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中最具影响力的作者之一。他与杰罗姆·桑斯共同创立当代艺术空间巴黎东京宫,并于1999年至2006年间担任联合总监。伯瑞奥德具有丰富的国际性双年展事务经验,曾参与策划莫斯科双年展(2005年联合策展、2007年)、2005年里昂双年展(联合策展)、2009年第四届泰特三年展、2011年雅典双年展等,并担纲9月12日即将开幕的2014台北双年展之策展人。
LEAP “双年展”的形式是否更符合您在《茎生—朝向一种全球化美学》一书中所谈到的“游牧性”?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是的,双年展首先是个“展览”,同时也是根植于某一特定文化背景的项目,需要在尊重某些在地规则的同时亦传递出具有国际视野的信息。双年展的策划与组织提供了一种际遇,使得展览本身与其承办城市(或国家)的在地状况相互协调,通过当地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来丰富展览的意义。所谓的“茎生”植物是一种在生长中不断从茎部生根的组织,比如常青藤。我想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一科属范畴的—我的“根”是无所不在的,由此我得以更好地理解他者、更快地去适应。LEAP 不久前您台北的演讲中提到,要避免将展览做成“任意一个理念或想法的示范”,如何才能真正避免这种情况,使展览本身“大于”双年展的主题、避免主题与作品之间的“插图性”关系?
LEAP 不久前您台北的演讲中提到,要避免将展览做成“任意一个理念或想法的示范”,如何才能真正避免这种情况,使展览本身“大于”双年展的主题、避免主题与作品之间的“插图性”关系?
尼古拉斯 的确。一般来说,试图对一个已存在的主题进行注释的展览是糟糕的。如果作品在展览中的功能是插图性的,那是对作品能量的一种截肢行为。因此,对我而言展览不是纪录片,或者说不是一个通过相遇的经历来寻找其主题的纪录影片。我的展览更接近“虚构纪录片”的模式,即它们反映当代艺术的现实性,透过某一图像或一个中心假设被组织起来。于其中,观看者可以选择跟随展览文本或者去创造他们自己的解读;也可以听取策展人的想法或者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作品上。就像在一出歌剧中,文本和音乐的地位是平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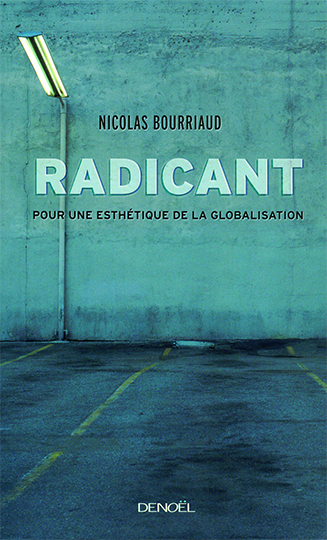
LEAP 本届台北双年展主题是“剧烈加速度—人类世的艺术”,您对“加速度”现象的态度是怎样的?它将如何呈现在展览中?
尼古拉斯 “加速度”首先是人类尺度的一种失败,它恰恰体现出我们在信息化经济系统前的一种无能为力。在这一系统中,各种决议都是以光速操作的计算模式来执行的(在美国,“高频交易”2已经占据了金融操作份额的四分之三)。“人类世”并非一个地质学概念,它亦指向这样一个时代,即人类已经成为他们自己搭建的基础设施的牺牲品。我们看到今天在个体/公民和其支配物所构成的新兴阶层之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盟:动物、植物、矿物质和大气层从今以后都被一种明确地脱离于公民社会的工业技术系统所侵袭。在“加速度”这个展览中,我集合了那些以不同方式来反映这种新型世界关系的各个层面的艺术家。
LEAP 在《茎生》一书中,您也谈到了热衷于寻找“根源”的现代主义的终结、全球化浪潮下当代艺术家新的“游牧”式创作与思考方式以及对于“移植”和“转译”等概念的兴趣。在这次双年展中,您对于“反人类中心论”这一观念的兴趣与您之前的“茎生”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延续性?
尼古拉斯 我的每本书都会启发我下一本书的内容,我的展览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依次连接的。比如,我意识到之前在伦敦策划的名为“另类现代”的展览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这次在“剧烈加速度”中意图探讨的主题,但当我开始策划那个展览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题目其实已经在那里了,就在众多的作品之中,只是我还没有看到而已。对我个人而言,一路延续下来的策展线索来自于对人类新的存在条件的一种持续探索,以及去询问这些新的变化是如何作用于艺术作品、如何作用于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组织与制作方式上的。但我的意图并非在于“反人类中心论”,对于这一观念我是持批判态度的。
LEAP 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关于“思辨唯实论”或“万物有灵论”这些热衷于“物”的哲学与美学思潮在当代艺术领域中的位置与影响?在艺术领域正在发生的那些实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对这些思潮的具体回应吗?
尼古拉斯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我个人对于所谓的“思辨唯实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展览并不是为水母或树木而做的,艺术完全是属于人类间相互关系领域的活动。相反地,这一新的关于“物”的思潮为我们的生态系统带来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它引发了一种将人类所处的关系领域延伸至“物”、至“生命体”、至我们周边环境的生态意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思辨唯实论”可以更新我们的观看方式,而在这次展览中引起我兴趣的则是这种被拓宽的观看方式与我在90年代所定义的“关系”(美学)概念下的各种实践之间的碰撞。在此我又将两者并置在一起看待并提出问题。人类人际关系网络的现实形式是什么?艺术可以跨出人类界关系的领域吗?至于说到“万物有灵论”—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一思潮引起了很多讨论—在我看来的确是处于“反人类中心论”立场的:“万物有灵”式的观点在于强调为“物”或“动物”赋予心灵,即为其提供人类的特性。看起来今天的艺术家们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并试着以此发展出更多不同的方向:从“物”到生命机体,从矿物质到工业产品,从植物的到数码的,从人类到动物……
LEAP 您在《双年展笔记》中提到,“关系艺术之所以遭到责难,就在于它还是过于倾向于‘人类中心论’的,甚至人文主义,所以在某些人眼中,才觉得关系美学难以忍受或者落伍了”。《关系美学》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结束与互联网的初步兴起,那么时下社会语境的变化让您对当初提出的这一美学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或调整吗?
尼古拉斯 这个展览的想法来自于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说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上的机器人要比人类多得多。在网络诞生25年之后,人类的确迷失了……由此意味着要对那些导出“关系美学”的理念重新加以思考。后者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恰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思辩唯实论”的诞生使得人类主体得以重新配置:那时候我们谈“结构”,今天则谈“物”。然而,如果从“物”的角度来观看世界,—正如“思辨唯实论”的支持者希望我们看到的那样,即是放弃以“关系”网络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凌驾于“认识”之上;同时,“物”亦超越了我们看待和思考“物”的意识。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思考框架出发,即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并不先验地存在任何等级的区分。但是从政治视角来看,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将生命体统统转换为产品、“物化”从未如此主导的时代,赋予人类以特权乃是十分重要的。
LEAP 自2000年以来,围绕与“关系美学”相关的艺术实践被赋予了很多不同的称谓,包括“参与性艺术”、“社会介入性艺术”等等, 用以描述这种参与性的或制造“关系”的艺术创作现象。您是如何判断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异?
尼古拉斯 参与性艺术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阿兰·开普罗、激浪派及后来的戈登·马塔-克拉克等艺术家和创作流派的实践。其主要目标在于拓宽艺术实践的领域,而并没有集中针对“跨人际关系”的形式和本质提出思考。“社会介入性艺术”亦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博伊斯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点…… 而(真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产生的新现象,则是出现了一批将“人际互动”的形式作为其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此外他们有时也从上述历史线索中汲取养分。参与性实践正如“社会介入性艺术”,这两者既是九十年代兴起的“关系艺术”的子集,也是后者的两个祖先。
LEAP 由您执笔的不同形态的文本与您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展览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写作者与策展人二者之间,是否前者对您来说更为根本和自然?
尼古拉斯 我尝试着让写作和策展工作不被艺术系统划分等级,也没有从属关系。我也始终在探索如何让这两者共生运行:一篇论述能够产生出一个或多个展览;同时一个展览也可以将我带至写作之中。比如当我在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策划“另类现代”展览的同时正在写《茎生》一书。两个不同活动的过程是相互呼应、彼此丰富的。当我想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会去做展览;当我有了一些答案,便会将之付诸写作。展览是一个提问媒介:它是一种聚合和合唱般的模式;而写作则是一个更为孤独和自我反思的过程。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正是在这两个位置之间作无休止的往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