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的执照:艺术学历
| 2015年02月21日
翻译 / 刘溪
“实验艺术”的标签自上世纪90年代产生之后,如今在中国诞生了新的意义。当时更鲜明地带有政治意味,而现在在学院的语境下,则登堂入室,标签最初的指涉也发生了变化—与其激进地与学院内其他系科割裂,还不如将重点放在跨学科式的工作和思维方法上。北京艺术家叶甫纳,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助教,她本科毕业于该校第一届“实验艺术”系—“实验艺术”系刚刚成为独立的学院。虽然并不像国外那样重视理论,但该院的研究生学位和博士阶段相较央美其他院系对技术的重视,它们已经算是更注重想法,且不要求学生只依靠单一媒介工作。当提到“实验”的定义时,叶甫纳有些犹豫:“我认为将‘实验艺术’视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在中国以外,我觉得人们不会称这样的艺术为‘实验的’,只会叫它们‘艺术’。我们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在这里仍然有相当多的传统艺术。所以相对而言这就是当代艺术。”叶甫纳在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毕业项目《家春秋II》(2012年)中,把对中国家庭老照片的分析视为对中国当代史的呈现,她在其中重现了每个场景中的人物,并同步播放对他们的访谈。展览以动态图像结合声音、数码相框的装置方式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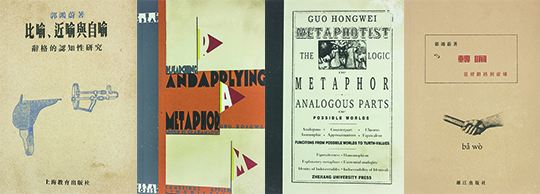
即便在理论与技术之间存在鸿沟,中国的艺术硕士这个相对较新的发展,也并非在真空中发展。世界范围内,艺术硕士是艺术界从业的必须受教育水准,并且表明了追求更专业艺术工作的态度。然而,中国的艺术硕士与这一定义显然有着差异:过去的几十年间,特别在美国,艺术硕士开始服务于更实际的目的—这个学位尽管并不能实际地带来被画廊的认可,但它仍然可作为一个功能强大的网络工具,为实际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在中国,拥有艺术硕士学位的艺术家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只是本科毕业。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年轻艺术家更容易以个体经验成功,就令艺术硕士的学位显得没那么关键。
近年来艺术硕士激增,对此最主要的批评是,年轻艺术家发现他们在学院坚硬的透明外壳下愈发难以将想法付诸实现。对这一变化持肯定态度的人相信这些读艺术的硕士生可能会对自身的实践有更好的认知,也对理论走势有更全局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将这个硕士学位视为社会特权的加剧— 这些学位通常不提供奖学金;又处在封闭的环境里,学生们通常更直接接触图像理论,很少尝试把技术与意义融合在一起。评论家戴夫·希基和杰瑞·萨尔茨指出,艺术硕士生并不想只是为了留校教书而去拿学位。在萨尔茨看来,目前的艺术硕士生,是“空白的一代”,被困在一个永无止境近亲繁殖和老调重弹的艺术创作循环里。(1)
“80后”中国艺术家,对“实验艺术”(或当代艺术)大多自学成才,这使得他们能够很大程度上逃脱理论的负担。他们几乎全毕业于艺术学院,其中少部分读艺术硕士。尽管如今的实验艺术系已成为一个选择,但大多数年轻学生仍倾向于选择一个传统的专业方向(通常是绘画),然后在毕业后再从自身的理论研究去钻研其他材料。何翔宇、郭鸿蔚和赵赵,目前这三位艺术家,尽管与以往艺术家不同,但并没有完全抛弃绘画,而是寻找多种途径去重新定义它。

何翔宇在针对展览现场制作装置时也会创作非具象的绘画,他不仅仅只关注画框内的空间,还感兴趣物品、空间、观者之间关系上,他的思考和社会意识,使得这些平静的装置作品直指感受力和消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赵赵利用油画和文献挑衅主体物,他没有可识别的风格,他的这种多元性挑战了艺术史留下的图像和形式,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郭鸿蔚则用水彩制造了高度逼真的图像感,颇似自然科学图谱,对各种物品进行归类,但也有不少物品明显脱离了自然科学理性的归类范畴。除此以外,他的实践还包括录像、雕塑、假书制作和手绘地图,所有这些都是对物的一种处理。当然,除了对媒材的使用,这些艺术家在作品中显露出特有的活力—一种常规训练以外的创造性冲动。
如果要继续论及当代艺术与学术之间的纽带,就得谈到富有争议的艺术博士学位了。虽然这个学位在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中有很大的区别,但一般都是服务于那些工作在艺术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人。大多数纯艺术领域的博士学位强调引领研究的实践,一个并不仅仅是理论书写—也把艺术家的实践本身视为一种研究。在美国,艺术实践的博士学位通常会与其他部门协作,如艺术史或电影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Transart研究所博士学位里有关创作实践的假期课程里,就把理论和实践的区别看作人为的边界。实践不一定以写作展开,但写作也可以成为某人实践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实践本身。
关于“艺术知识”与“艺术研究”的话语几乎很少在中国被正面提及。这些概念其实与艺术家吕胜中关于“实验艺术”的版本相距不远。作为央美实验艺术系的创始人,吕胜中意在提供一个涵盖观念艺术及非传统媒体的空间,为艺术院校和公众之间创造对话。尽管这个学院现在的确有博士点,但很少有学生有兴趣留在这个学术体系中。研究与写作是博士学位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是一定要和学生的创作实践有直接关联。
尽管实验艺术系借鉴了西方的艺术硕士课程,但又局限于其自身的语境里。导致这种矛盾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在艺术教育体制下的艺术学位仍然受制于标准化的考试入学模式。这意味着:当艺术变得越来越观念化及哲学化后,院校的艺术训练是否会更远离技能和技巧?写作是否会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正在朝向一个当代的观念,即艺术家更多以某种特定的身份兼具批评和思想探索,三者之间如有一座无缝的桥梁,自然会让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逐渐缩小。或许,当艺术的写作和视觉语言可以相互转化时,这就能开启真正实验性的大门。
(1)杰瑞·萨尔茨,《空白的一代》,纽约杂志,2011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