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装”的外来语:维吾尔之于凯末尔
| 2016年06月02日

在新疆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维吾尔语文字的下方犬牙交错地罗列着对应的汉语文字,就好像满嘴辅音发音的每一颗臼齿缝里都塞着一丁点焦糖渣。如果土耳其语系确有其源,那么这一支从巴尔干绵延到喜马拉雅的族群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断然不是以体量自诩的亚洲遗民的庞然大物。这个紧密族群的凝聚力源自口腔中呼吸与咽喉交界的柔软上颚之上,虽然这一栖身之处可能被不认为是属于体内用以传承的基因,但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词汇能比“Kêf-î Nûni” 以更独特的方式让鼻子与咽喉在频繁的发音中安分地躲在舌头之后。因此,当凯末尔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语言全盘罗马文字化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像“nasal [ng]”或是“velar”这样的发音会被遗弃的特殊现象并不属于偶然。

法国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将翻译定义为语言的包容性,既是包容外来文化融入其自身的语言,同时也是将自身的文化因素汇入到他者的语言之中。利科的上述定义,不仅抹去了“巴别塔”中一贯地有关人类种族差异、语言多样性和不可通译性的醒目注脚,更掀开了一页新的创世纪——在基督、伊斯兰及犹太三教共歆的神圣包容性之中,不同文化间语言 “兼容并包”的巧妙平衡和“世界在我口中”的福音终得救赎。如此说来,倘若将一词翻译成另一语言就犹如为家里的银器掸灰一般轻巧,那么直译(外来词)就无异于我们急忙忙要从妈妈的压箱宝中找出一件合适自己的衣服一样令人无从着手。我们的讲座“收音机的玩笑(2014)”就设定了这样一种状况,当外来词语义和语音的直译都大不尽如人意时,就好比身上的那件松垮的礼裙随时都可能滑脱一样尴尬。

在我们翻译“Molla Nasreddin”(也是20世纪初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出版的一本八页的阿塞拜疆讽刺漫画期刊的名称)一词时才第一次意识到,在前苏联的政策下,语言体系土崩瓦解的潮流不仅清洗了阿塞拜疆语,甚至连部分穆斯林的土耳其字母也遭到了破坏。在1929到1991这七十多年间,前苏联境内的土耳其字母至少遭受到了三次变化——1929年由阿拉伯字母变为拉丁字母,1939年由拉丁字母变为斯拉夫字母,1991年又从斯拉夫字母转为拉丁字母——在这一区域发动的字母战争,使得各民族不得已在自己的国家中进行流转。列宁认为,将前苏联的穆斯林语言拉丁化等同于对东欧的一次革命,因此他主导了对土耳其语系民众的全盘改造,将阿拉伯字母这一伊斯兰世界的文本记录从他们的生活中抹去。列宁并没有活到其继任者落实或者修正其政策的那一天,十多年后的1939年,斯大林最终因为对泛突厥主义的防范而选择了斯拉夫语。

字母表中第28个字母——通过鼻后小振动发音,如“ ڭ ”或“Kêf-î Nûni”——是那些并未完全从奥斯曼帝国文字脱胎换骨至土耳其罗马文字的幸存者中的一员。直到1928年,土耳其人依旧保留着两种“”的发音:其一是传统的“ ن (n)”,比如“never”、“nomenklatura”的头音,简单到你足以向你父母介绍;其二是“ ڭ”,一个极其古怪的“”发音,他在鼻腔深处发声,类似于“sing”的收音“”。“”音足以囊括所有东方技艺人的顶级证书,或者准确的说,勋章。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原因是,“Ng”几乎是众多中国姓氏中最常见的代名词,在维基百科的一项专门注解中写道“有名的人姓Ng”。但是在当今的土耳其,带有“”发音的词就好像是官方照片上的敏感人物一样被彻底洗去了——如:“Dengiz”变成了“deniz”(意为大海),“Tangri”变成了“Tanri”(苍穹)——这就算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毁灭,也是一个语音及语义学上一个令人沉痛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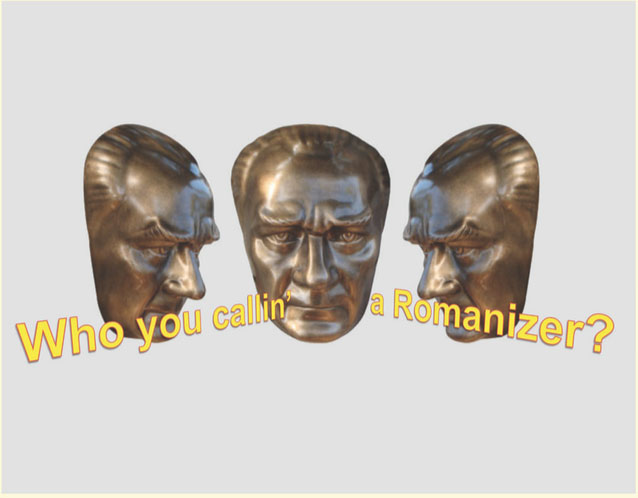
以我们自身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不仅仅需要四肢的灵活,也需要其他肢体的弹性,而不同的器官显然司职截然不同的作用。“Kef”一词在文字上是要体现出鼻腔中的两次抖动之间两个“”发音的截然不同。这其实迅速为我们点出了土耳其语系的亚洲血统,并且,仅凭字母“ ڭ”和濒临灭绝的发音“” 就足以在核心上揭露出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全盘西化政策对于这种血统的背叛。从中国到越南,横跨整个东南亚——这里并不是就移民而言——数以百万的“Ng”姓民众或许会问凯末尔:他为什么是一个扁鼻子蓝眼睛的老头?

在新疆,这个大陆远端的土地上,恐怕看不到任何一个“ü”、“ ö” 或是 “ğ”,它与如今土耳其的距离并不像直觉上认为地那么近。奥斯曼帝国在西进和向南扩展的过程中,却将其东部的一侧遗忘在了脑后。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长期居住的土耳其人长期受到敌对的俄国人管束;同时鞑靼人、切尔卡西斯人及其他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居民西进土耳其,而处在相反方向的东方故地却并没有被平等的青睐。我们不断默默培养、酝酿甚至苦心栽培的文化根源使得我们得以通过意识形态、历史地理以及口音紧密地结成一个节。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不加限制的异质文化的加入,阿美尼亚语、库尔德语、波西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鞑靼语都付出了沉痛的衰落代价。所幸维吾尔语却另辟蹊径,打开了局面。正如大卫·J·布罗菲所总结的那样:
大部分学术研究在涉及到有关民族社群的组成议题时,往往从分析其民族文化特性上入手,并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并最终落脚在主权民族国家之上。然而维吾尔族的案例并不是按照这个模式。在这个案例中,政治意义上的维吾尔民族认同限于任何形式的共识性民族意识。或者换一个略不同的说法,这一小部分被称为“维吾尔人”的人们发现,当他们以“维吾尔”自居时,实际上他们得以运用浓厚的早期中亚历史意味将更多的族群冠以此名并招至麾下。这样一来,就如“突厥”和“满洲”一样,维吾尔在成为一个民族名称前首先以意识形态出现了。

在维吾尔族群中发展轨迹的变化伴随着20世纪暧昧的中苏关系,唤醒了在前苏联领土上生存的土耳其人。那时,维吾尔人在中苏边界两端生活(现哈萨克斯坦区域)。在苏联境内生活的维吾尔人经历了1939年到1946年文字的罗马化,又在1946年被迫转为了斯拉夫语。在中国境内则截然不同,文字罗马化的影响在这里毫无作用,阿拉伯文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广泛使用。195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七个年头,随着维吾尔内部的自发行动和苏联的推波助澜,斯拉夫文字开始试行,我们十分关切的“Kêf-î Nûni ”或者“ ڭ”被改写为 字母“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在1958年的降温,这支改革火把在两年之后迅速熄灭,但随之而来的是基于新中国在全国推行的拼音系统改造的拉丁文字。

迈阿密Untitled傅览会,由Onestar Press出版
苏联解体之后,在土耳其的邻地上,其共同宗教的哈萨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以及吉尔吉斯人都历史性地建立了得以承续的民族国家。为什么维吾尔人没有如同上述民族一样?在1982年,阿拉伯文字通过少量的讨论和系列文件重新引入维吾尔语,这被认为是维吾尔人的一次胜利。但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却不难发现回归阿拉伯文字的举措极有可能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纷纷回归拉丁文字,维吾尔人在语言上没有为自己找到任何“西迁”的共通性。

在《反抗的艺术与约束》一书中,美国政治科学家与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关注了那些即便是在高压政权之下也能够逃离压制的口语、歌谣和手势。“通常”,他指出,“政治学家和学者仅仅观察清楚的、公开的或是有组织的表现,而这些绝大部分都可以被政府明令禁止”。他用“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一词来描述他所关注的反抗形式,强调的是在隐蔽处的内部政治。或许我们得以借用这个概念最字面的意义——“在舌头根的政治”——来生动描述维吾尔人、突厥人和波兰人及其他经历过文字动荡变化的族群的语言。如果要揭开政治、影响和社会在“字母政治”中的扭曲关系,我们或许需要的是一批鼻子、喉咙、牙齿、耳朵、嘴唇和舌头搅在一起的人。

(由曾羚炫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