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被召回的身体
| 2013年12月22日

音乐的属性关于时间,对声音体验则是失序的,即时发生又随机消隐。人类对其认知被压制在视觉经验之下,遭到依赖与漠视的,此刻又再度被唤醒。
策展人姚大钧对“声纳(SONART)”的构想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实现过。其发生的场所从演出场所到学院再到美术展览空间,它对媒介使用的开放态度在今天看来确实对多媒体、新媒体艺术具有启发含义。而在“转速:中国声音艺术大展”中,2003年在藏酷新媒体艺术空间举办的“北京声纳国际电子音乐节”被认定为是中国声音艺术发展的起点。彼时声音艺术尚未被明确定义,甚至被贴上“电子音乐”的标签。这是“噪音”第一次公然激怒国内观众,从公众到媒体都对这一新生音乐形态表示出好奇与无知。时间拨回2000年之交,姚大钧发起的“中国声音小组”和“前味音乐网”电台聚集并影响了第一批创作者。辗转十年后,中国声音艺术踏入全球的艺术现场,首次以群体形式的大规模亮相,此次展览是基于2013年3月在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每分钟转速:中国声音艺术十年”展的进一步发展,接下来还将在香港和欧洲巡回展出。
“转速:中国声音艺术大展”作为首届“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声音部分展出,并与建筑、影像、戏剧部分平行呈现。在整个双年展构架中, 2013年被认定为艺术进程中的重要年份。“中国当代艺术的20年”,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意大利未来主义声音宣言”诞生的一百周年—以此作为声音艺术发生的重要时间节点,将声音艺术正式纳入到国内的当代艺术展览体系之中。“转速”在字面上回应了中国声音展十年的加速发展和不断重启的过程,试图回顾并厘清历史脉络中的声音的位置。尽管声音艺术的评论者和创作者都反对为其赋予一个局限性的定义,声音艺术的定义始终悬置着—广义而言,“所有非音乐的创作都是声音艺术”;狭义上,“只有声音装置是声音艺术”(林其蔚《超越声音艺术》)。同样的,声音展仍以装置与“上海声纳”演出的两方面共同回应这一问题。
装置部分的展出空间是滨江旧工业遗存的4个油罐,作为非典型的临时展示空间,为布展带来了一定麻烦。4个巨型穹顶油罐划分为四个展区,展出来自中国大陆并加入了香港、台湾艺术家的声音装置和文献档案。以实验音乐人身份为观众所熟悉的王福瑞、王长存、徐程,新媒体学院背景的史文华、蒋竹韵、王仲堃、曾伟豪,以及作为评论者的颜峻、殷漪、林其蔚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悉数展出,作品涉及了来自空间改造、人文(人本)、社会等多种层面的议题:中国语音与方言调变(孙玮,《百子歌》),社会调查纪录,国际聆听公约(殷漪,《第一公约》),私密声音之空间对话(杨嘉辉,《室乐》),监听与权力(姚大钧,《罐听上海》);探讨后网络时代的声音生产的作品中,张立明(Hitlike)的《哈尔滨声音地图》是前web 2 .0时期实地录音的早期践行者,声音地图的建构与姚大钧将“啪啪”(类似可录音并即时分享的有声instagram)作为《社交媒体之声》的概念提出形成了文脉上的衔接。按照阿达利声音政治体的逻辑,这种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GC)诞生的全新的共时创作的声音体,正是由特定的社会形态下应运而生的声音形式。而在人民比特(RMBit)的工作中,截取这些社交媒体中大量的冗余信息并演化成现场的协作性表演显然是对这种形式的讽喻。在同一空间的并置来直观地检验三地声音艺术的发展形态与差距,而声纳部分加入的国际艺术家部分也为整个展览建立了更广阔的参照维度。同时,“中国声音档案”及“香港声音图书馆”也在整个展览中起到重要的文本作用。
另一层面上,从声音大展的LOGO已经在暗示这样一个概念—“声”与“音”的汉字合为一体,“乐”的缺席便是在强调,艺术与先锋音乐不能混为一谈。其中瓜葛如影像艺术与实验电影之辩,在全球声音艺术界论战已久。讨论声音艺术与音乐创作存在本体的差异性,但无法割裂声音与音乐两者的关系,其发生机制,物性和原理是相通的。国际声音艺术界强调物性、技术、论述,而对身体的漠视则被视作为当代艺术中知识对身体经验的背叛。声音是无法回避的可感知客体,暴露在外的耳朵永远是被动的,你可以移开眼睛,声音却让你无处藏身,“聆听”是其中最重要的动作,身体是无法缺席的。作为“噪音”的“声纳”演出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将观众拉回到聆听的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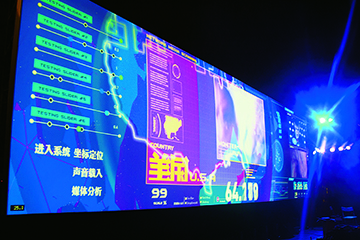
第一晚的声音表演倾向于声音视觉化的演出:社会媒体数据采集挪用与反讽的人民比特小组,Marco Donnaruma通过机械传动装置制造出的人体与科技杂交的肉体发生器;Edwin van der Heide的激光投影在空间中制造立体的声光幻觉;而第二天更加倾向身体性表演:杨嘉辉利用古典音乐发声机制与身体心率变化的合奏,探寻声响在物理和生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日本噪音先驱秋田昌美和深受harsh noise影响的虐待护士的反社会冲动;贾普·布隆的达达声响诗的人声即兴。演出的部分在整个大展之中不仅扮演着双年展开幕期间一次性的声音艺术事件,也提供了“作者与观众亲身近距离参与的、面对面的共时性仪式的机会”。在一场高分贝的噪音现场自觉祭出身体,开放感官通道,回归到艺术本源,达成接近萨满原始宗教状态的沟通。
在视觉艺术主导的双年展体制下,声音艺术家的发声始终来自外围。从来自黑暗空间(live house)爆发出的轰然声响,到进入美术馆的弱化,直至在公共场所的“消音”,声音艺术的创作者似乎也在避免过快进入体制(当代艺术的收编)而主动的自我边缘化。按照林其蔚在《超越声音艺术》中的梳理,声音艺术的历程始终是割断与接续的,从来不存在一条单一的脉络。而在与视觉艺术相交的线索中,未来主义宣言的启蒙、达达的声音诗歌、激浪等流派更迭之中,到近十几年进入美术机制的尝试……从噪音到声音艺术,作者对这种变化的质疑似乎隐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声音是作为当代艺术的媒介的一个预留的位置,在其他媒介的推进遁入困局时的另一方向。中国声音艺术大展的意义正在于,给予诸多问题一次开诚布公的机会,引起国内声音艺术家对现历史阶段的自省和警惕—激进的声音如何融入当代艺术历史的复杂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