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乾坤的图式
| 2015年05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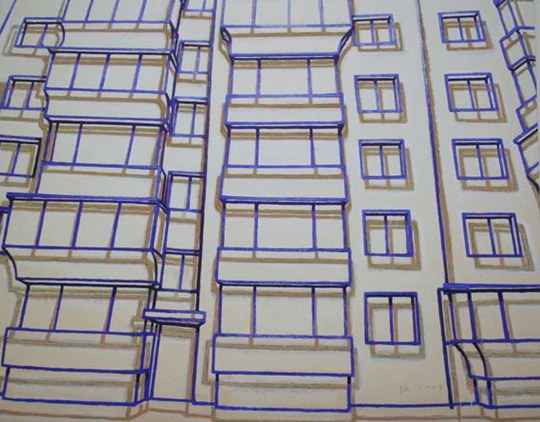
“未来政治的新奇之处就在于它不再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而是纠结于国与非国(人类)、单一个体与国家组织之间难以克服的脱节。
北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集体场景有别于西方大城市(如果把“西方”看作是审美和政治形式的一种标准,那么其中也包括香港和上海)。换言之,北京现有的环境代表了创造一种另类现代性最彻底的努力:完全有别于其他城市,但同时经济力量与政治空间等量齐观。它以不同的公共空间形式和对公共空间功能差异的划分,将群众组合为人民。在城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似乎预示了巴特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空无”这个东方主义式的幻想概念(他也这么描述东京),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真实存在的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空间的隐喻,它的确相当诱人:为聚集大规模人群而准备的宽敞空间,同时又是权力的中心。这种建筑形式表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某种悖论:强烈的阶级划分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并存,既是刻板人群的聚集之地又同时具有爆炸性。同时,还体现了某种中国式的本雅明思想,即文明和野蛮的相互毗连—我们的文明在此体现,我们的野蛮也在此体现。

风掠过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让人想起那些被拆掉的胡同。然而,“破旧立新”,是自革命之始就浮现出的必要理念,体现在北京的建筑规划过程中,亦是如此。辛亥革命后,主导城市规划的朱启钤所完成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为铺设新的道路而拆掉了一段城墙,这些新路就是我们今天环城路的开始。自古以来,北京城被玄学术士、诗人和都城的统治者看作是象征宇宙乾坤的一种图式——整个城市空间的实体设计、交通方式和建筑形式都对应于实体的、天地万物的层次结构:北京就是反射自然(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结构的一面人造镜子。这在当时是合乎逻辑的,那些接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人——朱启钤、梁思成、鲁迅、沈从文、 毛泽东——都对这片土地天人相应的宇宙价值观心怀敬畏。并且,把这座城市的重构当作是力图保留其内涵的革命性项目。既然创立现代中国的心灵是一种必需,因此构建激励新思维的城市空间也就非常重要。

北京曾经并且仍然是一个天地万物的图式表达。在这里,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把巫鸿论述中的“天安门”和“北京”的概念加以延伸,我们可以说,“通过重新解读传统建筑结构发掘这座城市的内涵,但是……主要还得从其物理空间上的浩瀚广阔来感受其内涵。”这座城市经历了无休止的解读,甚至剥皮见骨的严厉批评,与此同时,北京保留了其独特的身份。今天,北京的身份不再是那老一套的标签:紫禁城、蜜饯,或者词尾别扭的儿化音;北京现在连接着全球。在老城的空巢建筑,标示着政治权力与集体生活梦想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看起来无限接近,却又保持平行永不相交。

脱离了中国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北京是支撑的平台,天安门则是这一切戏剧性的中心。当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梁思成亲耳听到了这些话,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朱启钤曾经充满悖论地拆除式发展再次出现,而且以重建首都的名义规模更大。梁思成意识到了未来交通堵塞的问题,因此建议政府所在地应该挪到五棵松。毛泽东则坚持无论如何都得把政治的中心安置在中南海。太阳的能量强大,不能轻易放弃;众所周知,如果该能量确实强大到如此地步,自然会有人去利用它。试想,如何能在山高水远的地方盖一座水果市场?因此,即使冒着革命前的权力模式复辟的风险(这也引来了不少批评),新政府也必须留在故都的所在地。

这座丰碑、这座宫殿的城楼,其逻辑本身就包含一种不平等;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或者不一样的环境里。马克思对不平等的——他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看得相当清楚:由奴隶们建造起来的宫殿被村庄所包围,村庄则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其中也包括人。不论是否有价值,这个观点被许多革命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把它视之为一种启蒙性的观点,认为它揭示了一定的社会真相。然后,这些观念逐渐演变、融入了后革命时期的规划和建筑的政治。为了跟上新时代,老的传统被要求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造。当六十年代彭真任北京市长时,曾建议京剧所扮演的人物应该有所改变:
“六亿几千万工农群众(包括革命的士兵,即拿枪的工农)的伟大革命斗争,这么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么雄伟的建设事业,还不值得我们演?就那么几个死人值得我们演?”
上演新的集体生活的舞台当然是天安门。当毛泽东说在天安门检阅的时候应该处处烟囱林立,他的意思显然不是要把北京的市中心变成国家唯一的工业基地,而是说天安门是国家中心的象征,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其他地方息息相关。因此,六十年代这里的各种游行就没有中断过:毛泽东曾说,北京是他改变过的地方。

人性,太过人性
1949年以来,北京的人口和占地面积到底增长了多少一直存在争议;但至少我们清楚,这种增长体量巨大,而且一直在持续。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京把强烈的美学和历史特异性与“首都”特质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所在地,它的空间一定属于全体人民,而并不只是当地人。1949年,这座城市拥有两百万居民,占地700平方公里;今天,北京的人口估计有2200万,面积扩大到1.641万平方公里。城市的扩张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十年里;城市的主政者积极增加城市人口。中国这个象征性的中心正在快速地成为世界经济的象征性(真正的)中心。

让我们回到这个空间:封闭的堡垒与聚集人群的宽阔广场之间的对话——在某些特别的假日,大量品位庸俗的花盆被摆放在广场上。不必重新考量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人的、感情的、所有的。应该清楚的是,早在1993年,北京作为新政治中心的国际潜力就被顶尖的西方(或者应该用“国际”一词?)哲学家所发现。权力和空虚(一种渴望具体化为当前存在、“任何个体”的空虚)之间面对面的对话,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起点:在中东,在欧洲的隐形委员会,以及在纽约、伦敦或者其他地方的占领活动都是如此。草根的能量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递过程中,获得了几何级数般的增长,开启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新视野,产生了社会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新观点。

首都
在一个合理有序的系统中,一个大洲的人和物与另一个大洲的人和物互相接触;正如精神分析所说,人生命里隐藏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落满了灰尘,现在却全部都暴露在这座城市的单一平台之上。它们之间的碰撞看似戏剧化,但并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习惯彼此。
一个天地乾坤的图式也许可以加强体验,把人类的经验推向极致;在这个自由的平台上,成千上万的丰富体验造就了对集体完全不同的看法,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耐心体验到的东西。更少的墙、更多的门、无限的渠道。被酒和风皮革化了的皮肤,是实体内在的蜡样包装,成为了互相关联的感受的网络—在任何部位按下去就能使之激活。
首都是一个人的应许之地,它像龙卷风一样搅动了一个大洲的心脏:人、物、观念,所有的材料都被吸进这个无底洞,被压碎,被加工,以全然不同的形式重现:米粒变成了果冻,矿石变成了摩托车。河流被吸干;沙子在城墙边上累积,挟裹着神经质的热量在午后哀鸣。我们将砌起墙壁,我们将把它们推倒,我们将重复这一切。
文:卓睿|Jacob Dreyer
翻译:彭祖强

